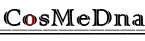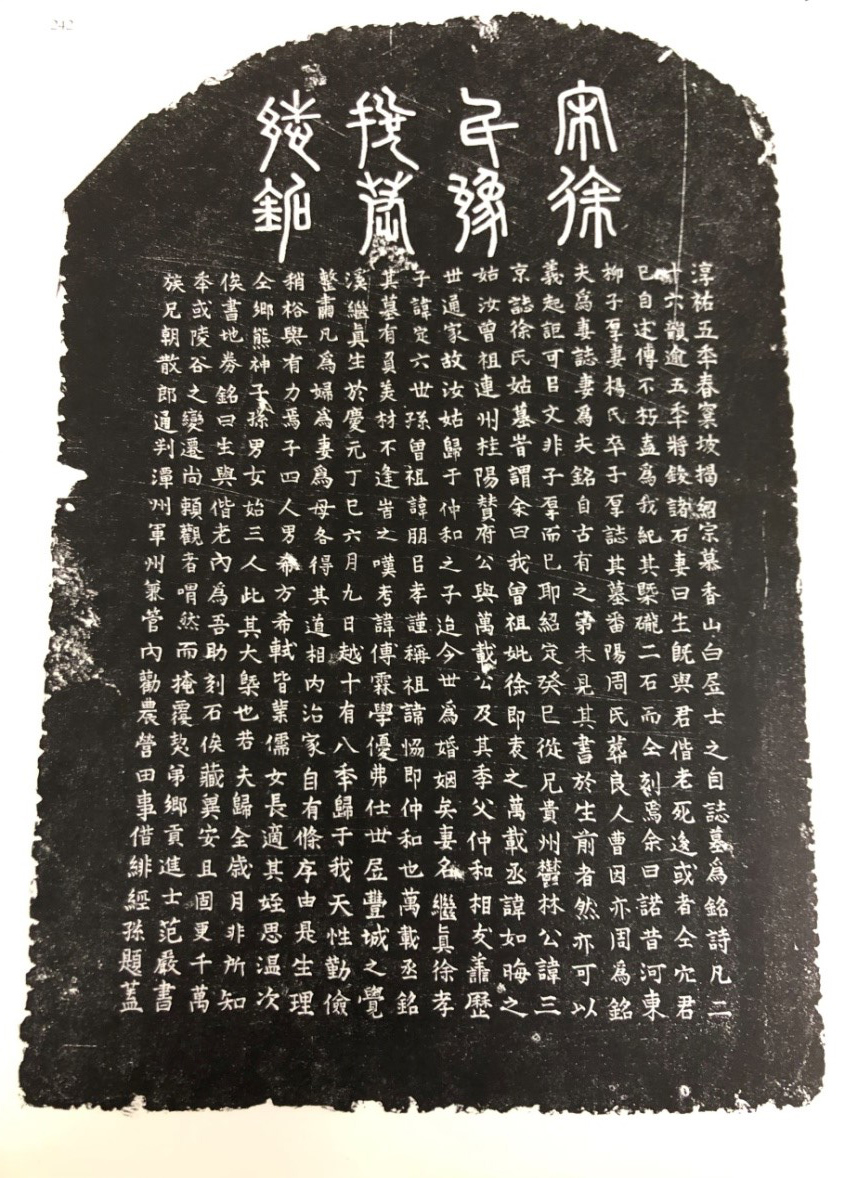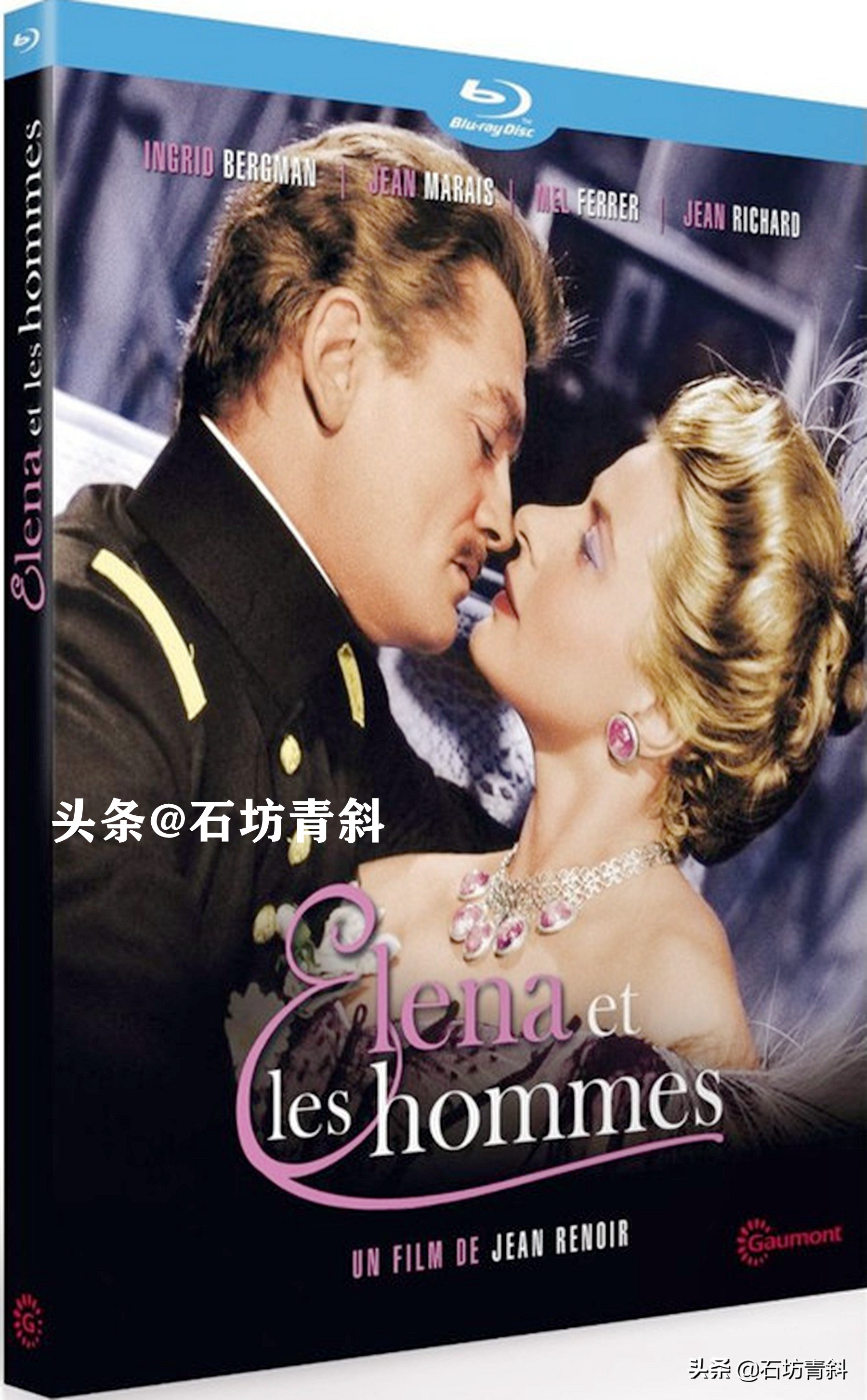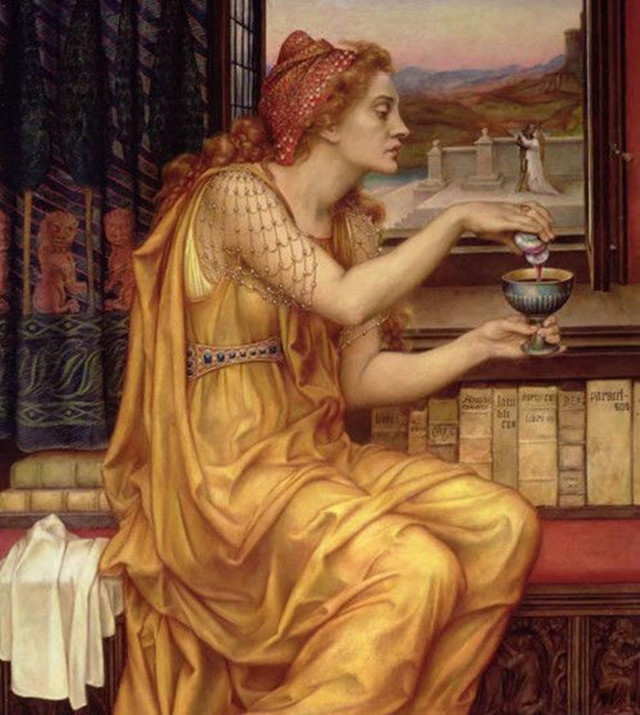本故事已由作者:肖爻悄悄,授权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发布,旗下关联账号“谈客”获得合法转授权发布,侵权必究。
1
打开微信,我看到了四伯的更新:二十年的人生沉淀,造就了今天的风光无限。配了图:九张照片里男人们无不腰如大鼓,头如卤蛋;女人们无不笑容灿烂,肥肉扩散。
众人在油腻腻的火锅店围着桌子站起来,举杯,个个衣着光鲜、面色俨足。我不知道步入中年的他们是否风光无限,我只觉得他们油光满面。
唯独四伯,像夹在牛肉汉堡里的一片薄绿的生菜叶,未沾肥胖、未染尘埃。
我在四伯微信下留言: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瘦?
四伯很快回复我说,因为妞妞想要一个帅爸比。
2
每年春节,我和爸妈都会倒两次汽车,再换乘一条船去爷爷奶奶居住的乡下团年。爷爷奶奶安土重迁的思想不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还表现在饮食习惯上:饭桌上永远是乒乓球大小的汤圆和金灿灿的炸酥肉。
大伯二伯和我们家早腻味了,提了鸡鸭鱼肉和城市里的各种特色美食孝敬两位老人家,只有四伯两手空空地往饭桌前一坐,埋头就开始吃汤圆。
亲戚围绕在饭桌上的话题年年都会涉及到四伯的终身大事。四伯结婚两次离婚两次,中间还有过好几个女人,都算了;养过一只法国斗牛犬,死了;至今他也一个人过。
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莺歌燕舞声中,我总能看见平静如水的桌面上逐渐浮现出一艘船。它载着家人对四伯的不满、愤怒、失望、轻视和怜悯绕着圆桌跑了一圈,最后在他的眼皮底下停住。
四伯看着船里那些板着面孔的形容词,冷冷地说一句:“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许你们眼里的终身大事,在我眼里只是屁大点儿的小事?”
“屁大点儿小事?!”大伯摔掉手中的筷子,“屁大点儿小事你都做不好?!”
四伯却淡然地举起筷子,分别夹了一块酥肉放进爷爷奶奶的碗里,无视大伯道:“爸、妈,今年的酥肉炸得特别好,外酥里嫩。”
吃过年夜饭,我爸把四伯叫到屋外阳台,聊了几句就掏出皮夹,取了大约一厘米厚度的百元钞往四伯手里塞。四伯也没推诿,接钱的动作和接过一个苹果一般自然。
接着,四伯从牛仔裤里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软装笔记本,递给我爸看,里面写满了诗。我爸翻了翻,沉默着,只用脸上的表情说话。
这场面让我想起了梵高和提奥。梵高的弟弟提奥一辈子都在经济上供养着画画的梵高,我爸也一样。他坚信四伯是一块写诗的好料子,认定他是超越时代的天才诗人,不被认可和理解是常事。也不知道我爸背着我妈给过四伯多少次钱。
四伯刚点燃一支烟,就看见了门口的我。
“哎,耘子,炸金花不?”四伯单眼皮下的两只眼睛像车前灯般点亮了。也不知为什么,亲戚里十眼九双,唯独四伯是单眼皮。
“炸个屁的金花,不管输赢,还不都是我家的钱。”爷爷奶奶是退休老师,大伯是公务员,二伯是银行经理,所有道貌岸然的亲戚中,我只会在四伯和我爸面前说脏话。
“走走走,”四伯扔掉烟头,拉起我就往客厅里冲,“我告诉你,耘子,这个炸金花呀,就像生活,乐趣在第一,输赢在其次。”
3
第一次带我接触炸金花的人,正是四伯。那年我五岁,念一年级。
那时四伯二十出头,很瘦,一米八的个儿,一头天生卷发,一对招风耳,背微驼,臀微翘;胯上洗旧的牛仔裤总是松松垮垮的,一副女人皮肤下垂的模样;上身总穿一件屎黄色的夹克,脚蹬一双刷得雪白的球鞋,总是隔三岔五地往我家跑。
每次他来,我都会凑到他跟前,摸他夹克的左口袋,再摸右口袋,以为里面有糖、果脯、肉干等小零食给我,但每次摸到的都是香烟。有次我怒了,将香烟用力摔在地上,冲四伯发脾气道:“你干嘛总来我家啊?”
你干嘛总来我家却不带礼物给我啊?这句话,我没好意思直接说。
四伯当然懂我的心思。他捡起烟,抽了一根衔在嘴上,微微一笑道:“因为你家客房的床总是空的,厨房的冰箱总是满的啊。”
下一次,四伯来我家的时候,夹克右边鼓出了一大块。我开心得不得了,摸出来,却是一副扑克牌。
“耘子,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说出去的人学猫叫、学狗爬,怎么样?”四伯锁上我卧室的门,拉上窗帘,把日光和喧闹隔绝在外。
我妈买菜去了,我爸还没回家。四伯打开我做作业时用的台灯,在灯下“哗啦哗啦”地洗牌。我点了下头,既兴奋又有些害怕。
“你的存钱罐呢?拿出来。”四伯洗好牌,把牌放在写字桌上,埋下头点燃了一支烟。房里的气味立即很难闻,烟头上的火星像一头怪兽发红的独眼。
“干嘛?”我警惕起来。
“下底注。”四伯不耐烦地瞥我一眼,从裤兜里掏出五块钱,“啪”的一声拍在桌上,“我现在说游戏规则。你只要用眼睛看,用脑瓜记,再闭上嘴,听明白没?”四伯弯起食指,用力弹了一下那张五元钞票,崭新的钞票像一只展翅的鸟儿朝我扑来。四伯拉开写字桌的抽屉,把烟灰弹在里面,抬起头看着我,“赢了,这钱你拿走。”
我当即砸烂了我的存钱罐,捡起里面的钱,数了数,有三块七毛,都是我一毛一毛攒起来的零花钱。
“耘子,咱们先说好,如果你输了,认命。输就是输,女儿有泪不轻弹。”四伯从我那堆角票里拿出一张,扔在五元整钞上。
“当然。”我嘴上这么说。当然,我不会输。我心里这么想。
结果我输得一塌糊涂,哭得泪流满面。
“我要告诉我妈。”隔会儿,我抽噎着,手指向抽屉,“我还要告诉她,你把烟灰磕我抽屉里。”
四伯一阵惊慌,但很快镇定下来。他将那叠一毛钞票塞进我手里,嫌恶地说:“拿回去拿回去,还是个小女娃呢,就那么人精。我最烦女人了。”四伯往椅子上一靠,拿手臂枕着头,大长腿猛地如同折叠床一样伸出来,那双雪白的球鞋就搁桌上了,正对着我的脸。
也不知为什么我就怒了。我将手里的钱用力摔在地上,并踢了踢旁边存钱罐的碎片,坚定地说:“四伯,你得给我五块钱!”
“扯皮吧?”
“你害我摔碎了存钱罐。买存钱罐的钱,你得赔。要不我告诉我妈。”
“那存钱罐顶多值五毛。”四伯瞟了一眼地上的碎片,鼻子里发出一声轻蔑的“哼”。
“你吃我们家,住我们家,剩下的钱,算在住宿费、伙食费里。”说这话的时候,我学着楼下开茶楼的王阿姨要债时的样子,抱起胳膊,拧紧眉毛,张大眼睛。必要时,我会用手指着四伯的鼻子。
四伯最后给了我那张五元钞票,并开始在来我家时,顺带捎给我一把糖果或者瓜子。后来我常想,或许这次事件是某种隐喻,意味着未来的四伯总在和女人的战役中节节败退,一路白旗迎风飘扬。
4
我念初二的时候,四伯和一个叫做刘雅素的女人结婚了。四伯母长得很美,但我妈说,感觉四伯媳妇的性格轻飘飘的,四伯拴不住。当时我还以为,四伯还没成为家里的顶梁柱。后来才明白,柱子是拴不住女人的,钱才能。
当时我念的中学离四伯家很近,走路只需几分钟。初三那个夏天,我妈嫌我回家远,给了四伯一笔钱,管我午饭外加去他家午睡,我得以窥视一对年轻夫妇的日常生活。
四伯平时总是一副匆忙的样子,只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四伯成了家庭煮夫,中午做炒土豆丝和番茄炒蛋给我吃,每天如此。
我馋肉,四伯就从冰箱里捞两根香肠来煮,桌上就能多出一盘肉。我还是嫌烦,向四伯抱怨菜太单一了。
四伯不屑,说你懂什么?单一才能专一。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下次让你吃炒土豆丝时能吃出薯片的味道,吃番茄炒蛋时能吃出鸡肉的味道。我“切”了一声,抬头看到饭桌边四伯母的脸,发现她的妆化得更美,脸也越来越好看了。
某天我忘带放在四伯家的练习册,折回去取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四伯在家。他躺在沙发上,抽着烟,看着一本泛黄的书。
“四伯,你不上班的吗?”我踢了踢他悬在沙发外面的鞋底。
“你回来干嘛?”
“拿作业本。你呢?”
“拿包。”四伯坐起来,目光黯淡,像瓦数不够的灯泡。
“呸!”他说这话倒是提醒了我,我从未在四伯家里发现任何男士包。我起了疑心,凑近他问,“四伯,难道你没上班?”
“耘子,我只是在家里上班,自然有人把钱打我账户上。”
“你是鸭子?”
“这倒是个赚钱的好办法。”四伯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把书搁在茶几上,转身进了厨房。我拿起那本书看了一眼,是一本《乐府雅词》,我翻了会儿,觉得无聊,很快就放下了。
离中考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我妈索性让我搬进四伯家里筹备中考。四伯一室一厅的家太小,只好把卧室里的梳妆台和衣柜搬进客厅,转而填进一张单人床。四伯、四伯母的双人床和我的单人床中间拉了一根绳子,上面挂着一片薄薄的白底红花的帘子。
当天我回到家,吃过晚饭后在客厅里复习课标要求的几首《古诗十九首》,四伯则不知从哪儿搬来了几盆月季、牡丹、山茶和仙人指,拿着小铲子在阳台上忙碌着。
墙上的时针跨出一大步,天空将黑夜推出舞台时,我才忽然意识到四伯母不在家。我从书里抬起头,朝着仍旧在阳台上料理花花草草的四伯喊道:“四伯,你媳妇呢?”四伯不应,我又对着他的后背喊了几声,他还是没吭声。
我起身走到四伯面前,看见他低着头,两手按在一盆月季的盆边上,好像在嗅那朵红艳艳的花儿。月季的花瓣上沾满了露珠,显得娇艳迷人。
“四伯,花比你媳妇还好看?四伯母呢?”我拉了拉他的胳膊,头顶的灯光正好落在了他的脸上。
我这才发现,月季上沾满的不是露珠,而是四伯的眼泪。
想起四伯母最近总是打扮得过分光鲜漂亮,我猜她准是和其他男人跑了。我呆呆地凝望着一言不发的四伯,不知道该怎样安慰这个男人,我记起一个小时前背诵的“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不知道该怎样理解这句话。
离中考还有一周的时候,四伯从家里失踪了。大半年时间里,家里人谁也没联系上他。
有次我妈在饭桌上提起,说四伯脑子进水,房子的产权写的是刘雅素的名字,四伯的所有衣服和书被她扔出了门外,还是我爸替他打包带回家的。
没过多久,刘雅素再婚,生了一个女儿,至于四伯,不知道飘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也不怪人家刘雅素,你四伯不出去工作,靠老婆养着,一天到晚就写什么破诗。哪个家庭能这样坐吃山空呀。”我妈说着,夹了一筷子炒土豆丝给我。
窝囊丈夫从不养家,还好房本写我名字,我潇洒离婚赶他出门。
“唉,”我叹了一口气,“我还记着四伯做给我的薯片味的炒土豆丝呢。”
“得得得,我炒的土豆丝不好吃吗?你四伯就是这样,不吃正常的菜,不过正常的生活。”我妈有些愤懑,“他那样的Loser,不值得记住。”
我吃了一口土豆丝,还是想念四伯。
我妈忽然又说,还是记住四伯好点,以此为戒,不走同一条错路。
5
高二那年,我迎来了不尴不尬的反叛期。我开始翘课、喝酒、和老师作对、同男生鬼混。我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自以为特立独行,实际上只有我自己清楚,我是承受不了尖子班的压力,应付不了习题和试卷的折磨。
那段时间,我最爱去的地方是离学校仅两个站的一家电玩城。闪烁刺激的动漫画面和喧闹酷炫的游戏音效让我着迷,对于一个想逃离现实的人来说,不现实的东西是最美好的幻象。
在所有的电玩游戏里,我最喜欢玩格斗类的拳皇。在KO掉对手,看着对方倒下的那一刻,小小的虚荣心和认同感在我心里炸出了一朵蘑菇云,我能看见云里探出无数只举着大拇指的手,对我点了比32个还多的赞。
某次经过游戏厅靠墙放的一排老虎机前时,我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卷发、招风耳、背微驼,穿着一件屎黄色夹克的中年男人。他叼着一支烟,专注地盯着屏幕,不停地往投币口塞游戏币。
“四伯。”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四伯转过脸来。我觉得他一点也没变老。
“你还喜欢玩这个?”我拉着四伯穿过人群,来到一台格斗游戏机前。中途四伯走得很慢,像在思考什么。
“对啊,刺激。”我在椅子上坐下,拖过旁边的一把椅子,“玩一局?”
“好。”四伯坐下来,低下头拍了拍牛仔裤的裤腿,有些心不在焉。
“投币啊。”我催促。
“你替我投。”四伯还在拍他并不脏的裤腿。
我顿时明白了什么。在我弯下身子投币的瞬间,我忽然想起四伯大半辈子都没拒绝过什么,他只是接受,接受漂流的生活,接受失败的爱情,甚至接受玩游戏都得让侄女买单的事实。
我被四伯接连KO五次,怒不可遏。
“你就不能让着我点?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就没让过我。”我耍起脾气来,又想起小时候四伯带我炸金花,赢光了我所有零用钱的事。
“让着你?那还有什么好玩儿的?”四伯掏出烟盒,“被KO掉的时候,应该站起来,拍拍屁股,说一声‘I’mOK。’。”
我瞪着他。
四伯却笑了:“不然这些年,我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忽然失去了发怒的资格。这几年,四伯到底经历了什么?
“耘子,放学后我来接你。你还在上学吧?”四伯的表情不怀好意。
“你要干嘛?”
“去你家。”
我知道四伯又没钱了。
6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把四伯请进家,就是请进了一个巨大的麻烦。四伯在我家一住就是大半年,活生生成了一个混球和无赖。
四伯在我家走出走进,不找工作,无所事事,每天只是吃吃喝喝,有了钱就去楼下的茶馆搓麻将,输光了回到家,又抱着我爸的笔记本在网上打牌。
我妈气得不行,在厨房故意把萝卜切得“剁剁剁”老响,还配上了四伯的名字。不远处,坐在沙发上看《快乐大本营》的四伯佯装不知,仰着脖子放肆地笑,笑声一浪接一浪。
几个月后,昔日的四伯母来到我家,进门就冲进厨房找菜刀,扬言要剁了四伯。我妈及时拦腰抱住她,不停地宽慰道:“我也早想剁了他,不过现在不是时候,他出门打麻将了。”
四伯母丢下菜刀,靠在我妈身上大哭一场,哭过后,才断断续续告诉了我们事情的原委。
就在几个小时前,四伯去了四伯母居住的小区。他了解四伯母的生活习惯,熟悉曾经的居住环境,因此躲进了家门口转角的安全通道里。趁着四伯母出门扔垃圾的当儿,四伯冲进家里,砸烂了电视机、踢翻了冰箱、还把碗碟和盘子摔了个稀巴烂。正当四伯跨到沙发上,一边跳着狂笑一边泄愤地大叫时,一团粉红色的东西弹了起来。四伯惊得脚一歪,整个人当场滚下了沙发,左脚也肿出荷包蛋大的一块。
穿着粉红色外套,留着娃娃头的小女孩既不害怕,也不哭闹,只是眼睛长了脚,四伯一瘸一拐地走哪儿,她的眼睛就跟哪儿。
那单眼皮,那小眼睛,那招风耳。四伯用眼睛一扫,基因二维码就显示出这是他的女儿。
四伯想也没想,上前一步,抱起女儿就走,正好在门口撞上了四伯母。四伯母还没反应过来,四伯就沿安全通道跑没影儿了。他明明崴了脚,却还能跑那么快。
“那房子本来就是他的,他当初主动给了我,后悔可以,拿回去好了,但他不能拿走妞妞。”四伯母的眼泪又快落下来。
我和我妈这才知道,四伯还有一个女儿。
“你们以为我不爱他?但爱情喂得饱生活吗?有了妞妞以后,和他更没法过。”四伯母擦了擦眼角,离开前说了一句,“如果他还回来,告诉他,妞妞喜欢念儿歌。”
7
四伯抢走妞妞后,带她去了乡下的爷爷奶奶家。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河流船只,爷爷的旧烟斗和老花镜,奶奶的炸酥肉和大汤圆,这一切都刷新着妞妞的眼球。小丫头兴奋起来就背着双手,站在大家面前背儿歌:“小竹排,顺水流,鸟儿唱,鱼儿游。两岸树木密,河流绿油油。江南鱼米乡,小小竹排画中游。”
四伯拍一下大腿,大喊:“妞妞,以后爸爸改行写儿童诗歌!”如果我妈在场,一定要呵呵,你什么时候有行过?
爷爷奶奶开心地笑,眼睛都快淹没在满脸的皱纹里。爷爷抓过四伯的手说:“有个孩子放你心口,心就不会乱了。”
一周后,四伯带着妞妞回到我们家,还给了我妈一大袋炸酥肉。爷爷奶奶给了四伯一笔钱,他准备从我们家搬出去,在菜市场摆个摊子卖卤肉。我隐约觉得四伯的生活开始了,真正的生活。
“妞妞呢?”我妈问。
“孩子还住雅素那儿,我已经和她商量好,想孩子了,可以随时去看。”
我妈点点头,像所有第一次向孩子提老套问题的大人一样,问妞妞,喜欢爸爸多一点,还是喜欢妈妈多一点。
刚满三岁的妞妞转着肉丸子般圆溜溜的眼珠说:“喜欢爸爸多一点,喜欢妈妈也不少。”
众人大乐。
四伯走过来,把妞妞举起架在脖子上,在客厅里转了好几圈,开心地放声道:“小宝贝,我输掉了生活中所有的筹码,但我赢得了生命中的你呀。”
我忽然想起初中时候背的那句诗:以胶投漆中,谁能别离此。或许,它说的不是爱情,是血脉。(作品名:《谁能别离此》)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
(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5759782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