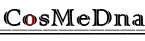本文作者“CUT”,欢迎去豆瓣App关注Ta。
第一章 雅克-路易·大卫的现代主义
第二章 从毕沙罗到塞尚的现代主义

Pablo Picasso, “Dance of the Veils”, 1907
第三章 从唯物主义到立体主义再到抽象主义
“唯物主义”, 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概念,其与绘画艺术中的唯物主义概念的关系不可能轻易地被论证,除非有人认为构建意识形态(ideological)能渗透到理论的每个方面、每一个象征性设定、每一个表达、以及每一种塑造传统形式体验;与此同时,马克思在他的理论中,也逐渐减少使用和提到这种在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直到完全放弃这个术语。
修正主义者已经留下了这样的说法;对于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如果他们是嫌疑人、以及是以弗兰克·科奥蒂(Frank Ciotti)为首的批评家所声称的伪科学(pseudo-scientific),那么拉康(Lacan)和福柯(Foucault)的超主观修正主义( hyper-subjective revisionism )、以及所有的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t)文学理论的宠儿等等,其知识理论中的基本的、幼稚的错误,造成顺利地传递到今天的艺术批评开始衰落——即无法做出让他们正确的、最简单的价值判断。
此书的“立体主义和集体性”(Cubism and Collectivity)章节的结尾内容(他的结论就是一种叫嚣)仿佛嚎叫一般,尽管,有关布拉克和毕加索的合作岁月里的大小事,在威廉·鲁宾(William Rubin)的著作“塞尚与立体主义”(Cézanne and Cubism)一书中有尤其详细内容描述,但是克拉克依旧一意孤行地坚持他的观点,即毕加索开始并且领导立体主义,随后布拉克加入其中:
……立体主义绘画不是一种语言:它只是外在形象。如果它不是一种语言,那么自然不会存在两个说母语的人(这是一种伎俩)。很有可能,在1911年和1912年之间,评论家们最终坚持认为毕加索与布拉克之间有差异;甚至当时当他们说在立体主义中我们面临的这一点(与其他人相反)不是一种集合体而是一种层次结构。它是由毕加索参与并率先的二重奏(dyad)。(他后来的说法非常有特色,‘他是我的妻子’,是他对布拉克的说法。)
这种说法在几个层次上有着明显错误,但是这是作者克拉克写作特点,即他喜欢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使用那些即使值得怀疑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抛弃集合体概念是很异乎寻常的举动,但是前文中克拉克对十九世纪八O年代末和九O年代末的塞尚的大型(对他来说)沐浴者(bathers )作品结构布局关注时,没有讨论毕沙罗和塞尚的关系内容中有相应的呼应。 克拉克还有更多的讨论内容,但是一种社会政治解释并不会让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核心问题,在十九世纪八O年代早期发生的“印象主义危机”(crisis of Impressionism)后,为什么毕沙罗,雷诺阿和塞尚开始创作这样的一个主题。 当然在十九世纪七O年代时,毕沙罗和塞尚的关系如同“栓在一条绳子上”两个登山者一样。此外,布拉克一直保持着与毕加索的密切交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布拉克应召参战时结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克拉克在有关布拉克/毕加索的问题讨论限制在1911年到1912年。由此我猜测,也许克拉克希望毕加索是一位大丈夫,一个强大的人——所以自然不存在任何的集合性。
另一个不诚实的引用发生在“不愉快的意识”(The Unhappy Consciousness)章节中关于画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内容,克莱门格·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可以从“杰克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该*死*的斯大林主义者”言论中脱身,这显然是与克拉克本人交谈。克拉克应该未经考虑就使用了这些观点,甚至没有考虑到格林伯格自己早期左派/共产主义者背景。这说明了一个事实,当他们的左派良知被刺伤时,社会必须对这两名男子的诚实抱持怀疑的态度。 我很怀疑归根结底波洛克是否拥有任何明确的政治观点,即使如此,这些政治观点不会对他的形成作品中明显铺陈的标志结构(毕加索理想Picassoidal——超现实主义者),以及克拉克正在讨论的它们的发展带来任何影响。 布勒东( Breton)超现实主义愿景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经过约翰·格雷厄姆(John Graham)传到波洛克和罗伯特·马斯韦尔(Robert Motherwell)时,变得完全不重要,什么都不是。这些如空气,在所有的艺术家还有其他人生存社会中无处不在,但是波洛克的想法似乎比这些还要多得多。
尽管“伪造/假冒”(counterfeit)这个词语听上去不是那么有趣或愉快,但是当书中的内容接近一种密切的形式上分析时,我还是很赞同书中有关立体主义和波洛克的章节很多内容——更为恰当地说法是,分析立体主义的整个内容,只是在告诉我们,不管平面图形中的个性特色元素结构排列和几何排列如何、无论视觉错觉(trompe l’oeil )游戏和“诡计”(deceptions)如何、习惯如何倒置、在平面上可想象的光学原理如何等等,整个绘画艺术实际上,从皮耶罗·德拉·弗朗切斯卡(Piero Della Francesco)和莱昂纳多(Leonardo)开始到现在,画家们仅仅只是描绘出自然世界的结构,内容同时会涉及到他们的感受,但是完全不是崭新的事实发现。
这些都是将绘画的角色和作用本末倒置了。
那么最前卫的最先进的绘画到底对社会和观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用:它们站在超出我们双目视野的前沿,协同感知主体的能力一起同我们对抗,实际上,感知主体的必要性是从非集中化的观念通量中形成格式塔(gestalts),否则,这些观念将会在我们司空见惯的空间中致使我们的方向定位变得绝望和不稳定。 而立体主义所作所为则是,把在十五、十六、十七世纪时经常用来从底部开始渲染画卷体积的格里塞勒(grisaille)结构和方式中的某些特点传播开来,其中仅仅着重说明其相对肮脏的色彩,对颜色的极端抑制,以及作为塞尚成熟创作风格的劣势——在用于指示凸凹表面的所有可能程式编录中,将其展开在画面上,用它们玩弄着一些视觉错觉的游戏(一种我从未产生或丝毫兴趣的游戏)。 而1911-12年期间的“假冒”时期的所作所为是,试图将它重新组合在一起(在某种意义上),以适应习惯性(a-priori先验性?)的感觉轮廓,以及倾向于从这种朦胧和细碎反射光线流动、凸凹不平的、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表面上形成的体积整体。他们的多做所为正如克拉克所言,通过重新引入通过平面过滤的模仿光源、以及标志,其中客体轮廓不完全符合逻辑,但足够让眼睛熟悉一种在其体内可以意识到的想象虚构空间。 这些其实都是同义重复的内容,即所有的绘画空间都是虚构的,以及所有的绘画功能就是展示在面对自己时我们内在的感觉习惯,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认为把它们视作整体的极限来应用。
立体主义所取得的成绩,尤其在它最初阶段时,是用一种粗暴的、大胆的、直率的方式,连同一种从15世纪初以来一直没有看到的强迫力,把表达的基本轮廓推在我们面前(所谓的原始艺术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而且这里,即在1906到1908三年间,毕加索是真正的首领,而不是在1911到1912年期间)。 在这个早期阶段,与布拉克带来的诗意、音乐和哲学上的影响相比,毕加索重新发现一些最基本的图形资源、有条纹的、削减的拜占庭式的交叉影线和中世纪角度折叠外套的效果图等等,带来的却是粗糙、不精致和愚笨的影响,例如——还有很多其他的——把它们变成戏剧化草图式的投影,以及用于描绘四肢躯体等的草草了事。
这些“唯物主义”哈耳庇厄们一心想把我们所有人都监禁在一个广泛的、用语言控制地集体垄断的环境中,从而无法获得非文字体验的自由空开的空间(勋伯格说——“我呼吸着另一个星球的空气”),因此梦想是“一种结构化语言”,绘画作品是“一种结构化语言”,社会当然不让的还是“一种结构化语言”。为什么?——它非常适合经他们恶意篡改和取代的对艺术家们的宣传议程。 这种理论自然会遭到很多的人的反对,其中,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持有另外的观点。他曾经说过“我们不能说话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或者类似的话),其中他承认在语言图画中某些思想层面和角度并不存在,尽管“语法是自主的”,但是不是所有的思想或经验在语法上是正确的。
一个人不需要变成神秘者才能看到无法言喻的经验领域。梦想不是“一种结构化语言”,关于梦想的解释才是;同样的绘画也不是,只有对它们的解读才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都很欣喜,从莎士比亚到《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语言*暴*政的嘲笑被丢进令人兴奋滚筒式烘干机中,最后把它们变成花言巧语。 视觉是经验的主要纬度,正如拉丝金所说“查看,真真切切地看到,是地球上我们能做到的唯一有用的事”。

Jackson Pollock, “Lucifer”, 1947
所以本书中的最后一章,“保护抽象表现主义”(In Defence of Abstract Expressionism), 在我眼里是一种公然的挑衅,仿佛西班牙斗牛仪式,它是红色斗篷,而我们是被挑衅的公牛,结果红色斗篷取胜。然而,正如凯尔文•麦肯齐(Kelvin McKenzie)曾经断言说报纸上从来没有真相时:“如果看上去不错,听起来不错,闻上去也不错,那么我们就打印出来”时,遭到了来自莱维森爵士(Lord Leveson )的反驳。“一切都很好,“莱维森爵士说,“但是如果印刷内容包含了一连串不准确事实——如果它实际上是一个虚构的内容——那该怎么办?”
首先,抽象主义者又名“小资产阶级艺术家”(petty-bourgeois artists),是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Leninist/Stalinist)对于那些对自己阶级特性(déclassé)没有任何疑问的人的阶级定义。 这个阶级定义背后有很多的实际内容,但是通过阅读传记,和那些恶意和传播的所有的政治同情来了解,花费的时间过长效率不高;但如果在天国的一次晚宴上,我们可以在(比方说)罗斯科(Rothko)、高尔基(Gorky)、马姆维尔(Motherwell)和T.J.克拉克之间进行有关阶级意识的主题和革命政治中艺术家地位的圆桌对话,我会知道我的押宝会放在谁一边,同时也会知道谁会对所涉及的问题认识最深。
例如,艺术家罗斯科的父亲,一位贫寒的拉脱维亚药剂师,曾是一位“安静、聪慧、道德严谨、充满政治热情 ——一个比实际更理想化的人”,一位“因反对1905年的大屠杀而转向正统派”的“致力于持不同政见人士”,“强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使在俄罗斯当局‘禁止’这些活动时,也一直在我们家里举行会议”。他属于“一个被污蔑的社会团体成员……居住在一个经常对抗犹太人、尤其用真正地暴力对抗犹太政治人士(如罗斯科的家庭)的城市德文斯克(Dvinsk)。”
“他们一家住在一个充满贫苦的劳动者(种土豆的农民和木匠和陶匠)和贫民的城市里,而且因为雅各布的职业关系,和他原有的对正统犹太教的抵制,以及家庭对政治和教育的异常激越地参与和承诺,全家人曾经四分五裂、各奔东西。” 关于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这个家庭的儿子,“韦恩斯坦出(此人曾是罗斯科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的经济依赖)来了一个犹太哲学家,罗斯科,伤害滋生,爱变成恨--‘他不得不卖报纸和毛裤糊口,而令亲戚蒙羞’”。 以一个青少年身份,年轻的罗斯科“开始成为政治异议人士,就好像寻求一种同化方式,同时又不会背负背叛家庭和犹太人参与左派的罪名”。 罗斯科后来说,他的整个家庭“称赞和紧随俄罗斯革命”。“我却成长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罗斯科说。 后来的大萧条时期——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继续列举下去……因此,称罗斯科为小资产阶级(petty – bourgeois),简直是对他的侮辱。
而类似的故事适用于其他许多的抽象表现主义者。

Mark Rothko, “No.61, Rust and Blue”, 1953
整个关于“阶级”的讨论被用作为艺术家生活中的决定因素,致使艺术家陷入不相符、廉价和绝望的境地。“小资产阶级”是列宁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花言巧语式*恶意*诽谤。它是谩骂谴责的代名词,例如苏联党派*官*僚和党内官员们(party apparatchiks)用来谴责和抨击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Shostakovich)以及他的创作成功的歌曲“穆森斯克郡的马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the Mtensk District)的专用语。
以下引用克拉克在此书有关波洛克章节中的第一段内容,可以非常准确地说明他的评论策略:“现代艺术家经常脱离社会细节,不仅仅是为了陶醉于艺术作品中的‘至关重要的花哨’,而是体现了与阶级态度或风格的异常紧密联系,不是和阿基坦威廉公爵不一样,或者至少试图模仿那种风格——它的冷淡、明亮、贵族气派、和漠不关心。”(这样的说法听起来更像叶芝而不是波洛克,更不是所谓的小资产阶级了)。
接着许多页面之后,又写道:“我不会(回到时尚杂志中的照片)因为赞赏波洛克绘画而去贬低、牺牲另一个,或者甚至加入高级定制服装来玷污整个抽象主义绘画作品……”——波洛克的绘画作品“似乎适当地(以他们的装饰性)退隐或者降低到舞会礼服和短上衣,以及当地博物馆和严肃的金融业务中的黑色领结‘功能’”。
他竭力地继续安抚或缓和这些诽谤和辱骂,但是这些早已带来了伤害。
关于波洛克创作于1947年至1950年间的作品,他说:“任何抽象主义绘画作品,只要它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完成、处在一种无法掌握的文化中,都会遭遇到矛盾……社会现实的标志,最后它(抽象主义绘画)将把绘画作为一种书写方式,因此而写下一部我们任何一个人以前从未读过的脚本。”(难道克拉克在想象全球范围内盛行的涂鸦病?)
“但是另一方面,绘画发现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实现。自然(意指习惯)根本不会消失。它通过新的笔迹重申自己的权利,并用它写下了一个熟悉的脚本——一节、秋天的节奏、薰衣草雾等脚本”,(由于创作时引入了一种初始的自然主义形象,和与创作于1948年的作品“第1号”形成鲜明对比的装饰性,波洛克被贬低为败坏和堕落)
“时尚杂志上的摄影照片……说到了资本主义对文化的掌控:就是说,与具象创作比较而言,这样可以轻松地完成创作,并把它作为快乐新秩序的一部分......”
抽象艺术是“有害活泼的”……同时又必须受到保护……“一直到当其再次被发现而且再次被认定为共同财产或集体工作时?具体、适用、亲手实践;……”
“共同财产还是集体工作?”——克拉克自己问自己。
针对以上的言论,我们可以与巴内特·纽曼(另一个臭名昭著地“小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艺术事业中的石版画平版印刷行业进行对照,其中梅尔•波切纳(Mel Bochner)写道:——
“石版画平版印刷的概念是它书写在石头上”(纽曼)……“纽曼说石版画平版印刷是书写和解释……其绘画作品是写在石头上的文字。用于石版画印刷的石头……代表物质真实的重量。它是地质时期的产物,最重要的功能是可以把物理和形而上学‘画’在一起……伦理和审美团结一致。这是艺术家唯一的真正的‘主题’”。这项艺术是否打算成为或可能永远是“共同财产”或“集体工作”,非常值得怀疑。
对待现代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定义,克拉克的态度是漠不关心,因为它的内容是针对过去的时代和成就的挖苦嘲笑,这些都非常适合他的理论内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期间及以后,人们可以把迅速发展的早期音乐、奖学金制度及斯特拉文斯基音乐魅力等等,称为民族志或人类学思想体系;乔伊斯将用他梦幻风景的熔炉同化了所有的(主要的)印欧传统的语言(仿佛全世界(一座现代的巴别塔)的历史都在异口同声地总结、概括着荣格集体无意识发展史);毕加索肆意搜括基克拉迪雕塑、阁楼花瓶装饰、罗马殡葬装饰等每一次发展,仿佛西方文化中每一种视觉表现都是磨炼他杂食性食欲的胃口;韦伯和勋伯格重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代数对位和荷兰语复音的复杂性;很多很多,不胜枚举。
这不是现代主义者对古老的精神的生吞活剥行为,而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些早期艺术中存在的非物质、宗教内容和动机,最后心慕力追,开始寻求进一步的发展;此外,这些不是简单的怀旧和怀念,而是真正地试图担负起对现代“异化”和虚无主义的困境承诺,一种只能称之为宗教的和/或至少形而上学的感觉模式;因此因此斯特拉文斯基的皈依宗教(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返祖现象)和他后期大部分音乐作品中的男高音;同样的还有T.S.艾略特;勋伯格未完成的歌剧“摩西与亚伦”(Moses and Aron)中戏剧化的信仰危机;以及许许多多对二十世纪政治事件中出现的灾难性邪恶的反抗响应。(叶芝和奥登在很大程度体现了这些)巴尼特·纽曼的作品“十字架站”(Stations of the Cross),还有罗斯科的教堂。
这些情绪是是现代主义呢还是反现代主义?
如果没有他们的贡献,现代主义历史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二十世纪二O年代的斯特拉文斯基反现代主义则是另一种现代主义战略,充分说明了并不是所有的“务虚战略”都是正确的。

Barnett Newman, “Stations of the Cross”.
我写作内容终于转到了在抽象表现主义争议层面中浮出水面的克拉克“有争议”的说法“粗俗”,而且我不需要从字典中找出这个单词的,被克拉克用来支持其理论(这总是暗示使用者怀疑这个术语的适用性和安全性)的定义。 “Vulgar”意味着攻击那些自身培养的感性水平为表里不一的冒犯行为,与此同时将目标瞄准在假定对方比自己更低级/卑鄙(lower/baser)的品味和鉴别水平上。因此,瓦格纳是一个粗俗的俗人(尤其是在“帕西法尔”中),在戏剧中,为了从基督身份(或领主)身份高度冒充成为圣杯传奇的密封奥秘的大祭司,他屈尊为一位失去真正宗教信仰,同时又强烈渴望一夜之间能得到精神上的神示的资产阶级观众。
克拉克之所以将抽象表现主义描述为“粗俗”,因为他认为自己有一定品味和辨别力,即使他当时几乎没有获得任何支持和证明(不断推迟到克林门格林伯格和迈克尔·弗里德谈到评价的真理性问题时,他的观点才被确定下来): “看到波洛克更多,我的评价越高”; 在描述斯蒂尔(Still)的绘画作品时,死记硬背地用格林伯格的“抓眼球”(buck-eye)一词来评论,以显示自己支持立场;在给西德尼·詹尼斯(Sidney Janis)信中,他毫不掩饰对斯蒂尔攻击罗斯科行为的支持立场:“意味着激情,偏袒和具有倾向性,但是由于这个原因(因为它一度退出了受尊重的圈子),这应该是罗斯科至今受到的最好的批评。 ”
众所周知,格林伯格讨厌罗斯科以及画家的大部分绘画作品:“一个临床偏执狂”,他评论说,在他的厚达五卷的随笔文集中,唯一一次真正地讨论罗斯科的作品出现在“美国式绘画”(American-type Painting)章节中,当时他正在写文回应(Patrick Heron)关于他的一些可识别的美国特征内容的指控(由帕特里克·赫伦Patrick Heron发起),维护自己眼中的美式绘画小组,(此时实在是无法忽视罗斯科了)。

Jackson Pollock, “No.1, 1948”
当克拉克放弃自己的研究方法,他的有关价值判断往往漏洞百出。前面我已经提到了他如何贬低布拉克(另一个迎合奉承克林伯格的例子),但是当需要评论波洛克的画作“第一号,1948年”时,他又再次表现出他的散光视觉:
所以来这里我想说清楚。你会听到我赞赏‘第一号,1948’为一幅杰作,达到了我们理解能力的极限。如果我不得不选择一个现代主义的时刻,其中最完整地描述了形式和限度--最深刻最伟大的--代表一个时代的语言,或者是创造了一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刻,就是这一幅绘画。如果有人问我,现代主义和偶然事件的最终含义,我会指出朝着‘第一号,1984’指引的方向。
他还深入研究和高度赞赏这幅画中的“中央黑色飞溅的鞭纹与华丽的红色”局部,他还是继续说道:在众多的波洛克绘画作品中,我只会选择“第一号,1948”,放弃其他作品--即使放弃神秘威严的“一个,1950”——因为这幅画作精巧而且脆弱……”因为它“包含着自身内部的对立面”;因为它的“纠缠的画面和纸张的薄脆感”。 这些言语是否意味着相互对立,相互矛盾?但是:“我也不想做出这样的批评结论,认为这是一种审美品质的反驳”——但是,他刚刚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

Jackson Pollock. “One”, Number 31, 1950
“它的中心的中心,就是现代主义真心实意地坦诚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权力意志”……和波洛克其他的很多作品,其中包括“一个,作品第31号,1950”, “路西弗,1947”(Lucifer,长:104厘米,宽:267厘米),和“秋天旋律,1950”(Autumn Rhythm)等等相比较,“第一号,1948”(长:172厘米,宽:264厘米)实际上是一幅非常薄脆,易碎的小型画作。 创作于一年前或更早时期的作品“路西弗”(Lucifer), 是一幅更气势磅薄和(在我看来)雄辩有力的绘画作品。在克拉克眼中,“第一号,1948”是他主张的概念主义(conceptualist )的呼吁,而不是感性主义(sensualist)的申诉,因此对它的有点肮脏,干巴,灰溜溜,油炸后的极度疲惫不堪的意像视而不见,一意孤行地赞赏它。
某一天,请给我作品“路西弗”吧,请给我作品“一个,作品第31号,1950”吧;以及“世纪的代言人或创造了一个新世纪?”,这是多么夸张,疯狂,一厢情愿的想法!绘画永远无法做到这些,哪怕是妄想着绘画能做到,多少伟大的艺术家们连尝试的念头都没有。波洛克和其他任何的艺术家一样,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说出这样的疯狂的豪言壮语。艺术仅仅只能创造出一个传播者手中的时代,在创作过程中传播者们削弱和放低艺术身份,改造艺术,使其更适合被普罗大众所接受和理解。
此外,克拉克的“Vulgar”也包含着“华而不实”(gaudy)的的含义,并且与资产阶级超越幻想的共谋并行。如果美国最有天赋的色彩师(指罗斯科)都是“华而不实”的,那我们这些普通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这里的内容,正如书中的其他地方内容一样,克拉克评论策略是抓住艺术家或作家最薄弱的环节大做文章,并且用大刷子来来去去火上浇油。 我们相信,在罗斯科众多的创作中,肯定会出现一幅或两幅作品中罗斯科的配色可能会显得“华而不实”,但是绝大部分的作品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这少少的“花哨”配色,其中都是是由非常不寻常的卡其色,桃花心木,橄榄,瓶绿色,灰色的群青等等色彩来带的和谐,奇怪,微妙,灿烂和沉思等感觉,产生的总体效果是醇厚,媒染,丰厚和奇特,而不是人工糖精似的伤甜,尖锐,或“华而不实”。
与资产阶级味道同谋并存?根据斯蒂尔的说法……“他用他的野心和暴政攻击所有挡住他道路的人,令他人窒息……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明确地表示,他的作品来自于沮丧,怨恨和侵犯……”
也许这就是那些诽谤的人宣称的与资产阶级的品味相提并论的内容,或者如彼得·富勒那样用“用资产阶级的形象重塑成世界”进行总结,这样一来,恐怕会让罗斯科,他的画家朋友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超现实主义的极左派阵营中为他们的学徒服务),以及他的所有崇拜者和拥护者等等恐惧,并且通过只能通过超级具象的方式提及艺术家在最自信和自我放纵的时刻表达的观点和自我评价,才能够证实自己,艺术家在自己最自信和自我放纵的时刻所说的自我,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因此此时我们宁愿选择伴随着罗斯科成长的习惯,保持沉默。

Mark Rothko, “No 2, Yellow Red Blue on Blue”, 1953.
克拉克完全避开了罗斯科创作“西格拉姆壁画”时的崩溃和失意,而正是这个创作项目,这带来了罗斯科对自己未来的观众的最自我折磨的焦虑,也表明他非常了解,在一个物质世界里——一个克拉克要我们相信那是唯一的世界,艺术的超越是何等的脆弱不堪一击。 不可否认,这些内容的确是罗斯科后期生活和创作生活中所面临的中心难题和困境,他一生致力于追求艺术的超越,而自己也是在这种力量的带领下前行,直到自己完全地被钉在了自我受难的十字架上,这么说有人会觉得过去宏伟和耸人听闻,但是“庸俗”这个形容词根本没有任何的正义。 罗斯科的浪漫主义从来没有达到瓦格纳的高度和广度,罗斯科大约在1957/58年间开始追求瓦格纳(Wagnerian)派的一种粗俗风格(上面有所简略交代),但是他的浪漫主义从来没有达到瓦格纳的高度和广度。尽管处于不同的原因,我依旧广泛地分享了克拉克对罗斯科晚期创作的分析:对于我来说,1957年公开的作品中有部分作品其内容充斥着罗斯科的挑衅和攻击,而这些攻击挑衅的矛头直接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对他艺术的追捧和大事购买(说到底有什么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强硬派分子的解释更可能是资本主义),其中隐藏的悲观主义开始窒息和扼杀他的创造力,导致他的接近瓦格纳派的自命不凡的教诲宗教信仰无限膨胀,以及私人方面的深度抑郁,每当我们走近泰特现代美术馆,进入”西格拉姆壁画“展览室时,所能感受到的一切。
资产阶级艺术猎手似乎以“悲剧”和“厄运”为借口,津津乐道与其中的令人绝望的抑郁经历,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后大屠杀的宣泄,如果这是一个正确说法,到头来,那种光面弹簧的理由和借口就是玷污了罗斯科投射的自我形象。 克拉克完完全全忽视了所有的反抗,申诉和对抗。在任何情况下,(他们以为那些非常事是不存在的)当有更多的明显地需要得到指责的目标时,为什么偏偏要把指责的矛头对准抽象表现主义者对“粗俗”的矛盾指控。
敬请等待第四章
(全文完)
本文作者“CUT”,现居London,目前已发表了233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CUT”关注Ta。
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9897657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