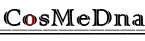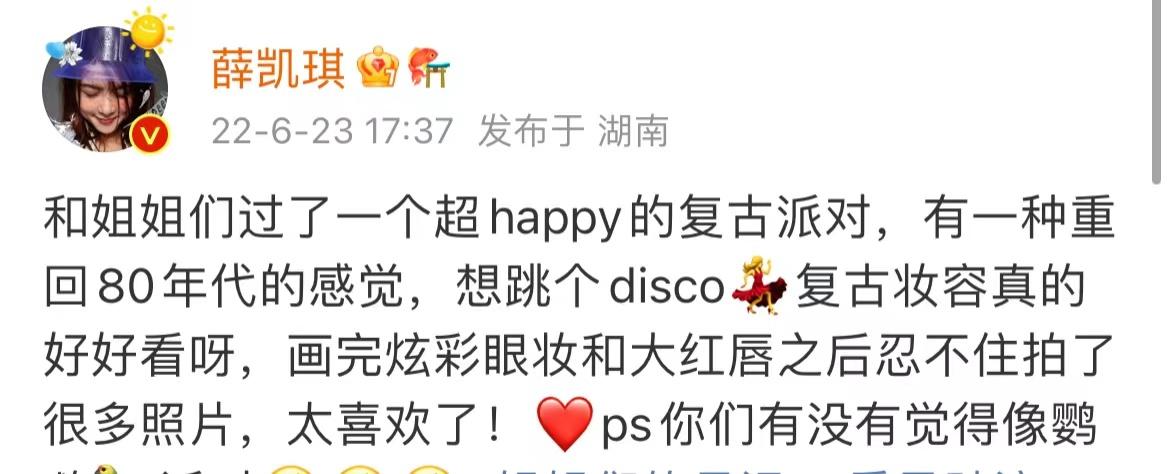假如要用一句话概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那就是魏晋风骨、唐宋风尚、明清风流。这个风流,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风情、风雅、风致、风貌,而是集大成式的贯通古今、出入雅俗、弥缝朝俚、周旋庄谐的一种精神创造。尽管这种风流,不再有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悲壮、大江东去浪淘尽的雄浑,不复见门前流水尚复西的达观、醉里挑灯看剑的慷慨悲凉,但是这个时代的风流却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人格形象:文人(才子)。这个形象或许有些瘦弱,在庭院深深的芭蕉树下独自沉吟,昨夜的笙歌,犹有一些余音散韵缭绕,然而,他的内心却沉浸在一个前无古人的精微细致、风雅自娱的境界中。
周晖在《金陵锁事》中记载李贽“好为奇论”,称汉以来“宇宙间有五大部文章”,汉是《史记》、唐是杜甫集、宋是苏东坡集、元是施耐庵《水浒传》、明是在当时享有盛名的“前七子”之首的李梦阳集。这种“奇论”表面上看是突破了典雅的范围,在典雅中加入了通俗文学《水浒传》,但在深层,是人格精神的一次提升。在近千年的典雅文化的熏陶下,李卓吾将《水浒传》与《史记》、杜甫集等并称,这种带有戏谑意味的背叛,是时人非常普遍的奇谈怪论。这种戏谑风格的文学观,在金圣叹那里就有了“六才子书”,把《离骚》、《庄子》、《史记》、《杜诗》与《水浒》、《西厢记》相提并论,更为甚者,他认为《水浒》可媲美《论语》,《西厢》可取代“四书”而作为童蒙课本,进入让俗文化取代了典雅文化所具有的庄严色彩。在明代湖北才子袁宏道的言论中,同样把《水浒传》置之六经之上,甚至把《金瓶梅》称之为满纸云霞的“逸典”,与古代典籍相提并论。这种颠覆性的观点,打破了雅俗的界限,但在内心深处,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追求的一种理想人格。
袁宏道在《与徐汉明书》中提到这样一种人:“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圣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这种奇特的精神人格,既贯通儒释道,又不在藩篱中,成为一种极其特别的人格形象。金圣叹曾有“岂不快哉”的妙论,和袁宏道的趣味论同出一辙。
金圣叹当然是才子,关于他的名字的来源,《管锥编》中提到是来自赵时缉《第四才子书.评选杜诗总识》:“余问邵悟非(讳然),先生之称‘圣叹’何义?曰:‘先生云,《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则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自以为狂也。’”孔子对曾点“暮春三月,游春沐浴,生机盎然”的人生理想十分赞叹。显然,才子们并没有背叛孔子,他们在传统学问中找到了“自适”“适情”的人生态度,在奇、畸、狂、放的人生言论和行为中,表达生命和安托自己的心灵。

在中国文学历史发展长河中,生命的感悟与自觉始终是永恒的话题。李泽厚先生认为,在魏晋时期人的生命的自觉,实现了文学的自觉。不能否认,在明代中晚期,总体上知识分子的心态是伤感的,这份伤感是来自于生命的又一次自觉。对生命短暂的感喟和对世俗功业的冷漠,最后在明代中晚期出现了一个高峰,又一次的生命觉醒带有享乐主义色彩,伤感却不绝望,热情而又冷静,构成了当时才子文化的社会精神生态系统。这些才子们寄情于艺术,并且把人生艺术化,用才华慰藉心灵,寻找共鸣,抗拒死亡,享受生命。他们不再以所谓的古穆典雅作为标准,而是以适情出入雅俗,创造出了才子式的典雅。他们既能诗书立世,又能游戏人生,在艺术化的生命里找到了出世与入世之间一个绝好的平衡点。
金圣叹在《水浒传》第十三回的评点中,认为“一部书一百八人,声施灿然,而为头是晁盖,先说做下一梦。嗟乎!可以悟矣。夫罗列此一部书一百八人之事迹,岂不有哭、有赞、有骂、有让、有夺、有成、有败、有俯首受辱、有提刀报仇,然而为头先说是梦,则知无一而非梦也。大地梦国,古今梦影,荣辱梦事,众生梦魂,岂惟一部书一百八人而已,尽大千世界无不同在一局,求其先觉者,自大雄氏以外无闻矣”。这种人生如梦的叙述,强调了金圣叹的文学观:“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他觉得,世事如白云苍狗,生命如夏花晨露,水逝云卷,风驰电掣,短暂生命总得有各种消遣法,以遣有涯的人生,种田耕读是一种消遣法,隐逸山林是一种消遣法,雕虫小技当然更是一种消遣人生的法门。
在金圣叹的理解中,所谓文学艺术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无疑是欺世之论,但作为生命的印记留赠后人,“不可以无所赠之”。这种强烈的生命感受和对自身个体的高度关注,使得金圣叹这样的才子不会遁入空门,恰恰相反,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表现得格外强烈,甚至在生活的细微处,也表现出那种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热度:“冬夜饮酒,转复寒甚,推窗试看,雪大如手,已积三四寸矣。不亦快哉!夏日于朱红盘中,自拔快刀,切绿沉西瓜。不亦快哉!”这种对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品鉴,充满了哲思和情趣,成为当时才子文化的鲜明特征。这个特征表现在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过程中,中国的传统艺术,如诗词、书画、文玩、园林、戏曲、家具被有机地统一到一起,他们并不是单纯的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而是消遣生命、滋养心灵的一种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唐寅、文徵明等创造了书画艺术的高峰,但从更广阔的背景上看,这只是生活艺术的一部分而已,它并不是孤立的一种艺术创造。
众所周知的是,江南四大才子无一不是“千古才情万古对”,才华超群,书画绝伦。与此相映成趣,更出名的是唐伯虎点秋香这样的穿凿附会之传说。与此同时,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出现了才子佳人小说。才子文化其实是一种人格文化,是表现生命理想、兼容书画艺术的文化样式。才子文化具有很强的二元化特征,既有强烈的精英文化的气息,同时又有强烈的世俗性特点,精英见其超拔,世俗见其华美,但在脱俗与世俗的互动中,形成了“才子”的一段风光旖旎的文化风景。
诚然,明代文人才子的社会地位已不再像宋代那般“礼敬名儒”,“文字狱”与“八股取士”制度大大打击了文人士子的积极性。文人阶级发展到明代,已然开始分流:庙堂、市井、山林。一部分文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来赞扬当朝者的伟业,从而获得在朝堂上的话语权,另一部分文人则是从政治路途上的无望转为将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文学素养等寄托在文化与艺术实践中,对自我生活环境进行升华。“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纵使易之,亦未必有补于品格也。”可见文人已将自身的审美理念借助身外的“长物”来展现自我,追求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明代的江南文人之中都普遍流传这样一句话:“备它一项轿,讨它一个小,刻它一部稿”,“选声伎,调丝竹,日游佳山水”对他们而言,“风流文人”是不拘于庙堂之中的,他们崇尚的是随性自在。在一间陋室之中,一个小妾红袖添香;园林之中,有一顶软轿可供赏玩代步;在自己精心布置的书斋之中,刻画一部书稿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就了。这种悠闲享乐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文人致力于造园、家具赏玩等情趣活动中,力求追逐生活的精致化。

陈继儒在《太平清话》说:“香令人幽,酒令人远,石令人隽,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闲,杖令人轻,水令人空,雪令人旷,剑令人悲,蒲团令人枯,美人令人怜,僧令人淡,花令人韵,金石彝鼎令人古”。 这些感受从何而来?这是情感专注后的发想。正如中国古人所说“情深而文明”,这种种对事物情韵和趣味的感受源自于文人对生活中美的事物细腻的体会,更是文人自我内心丰富情感的深切表达。于是文震亨也说:“高梧古石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俱冷。故韵士所居入门便有一种高雅绝俗之趣。”
这绝俗的高雅区别于表象的伪装,不是装腔作势,更没有矫揉造作,而且无论在怎样的生活条件下,已成为文人情感的要求和心灵的回归,是文人韵士才情涵养的溢现。沈春泽在《长物志》序言中说:“司马相如携卓文君,马车骑,买酒舍,文君当垆涤器,映带犊鼻禈边;陶渊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丛菊孤松,有酒便饮,境地两截,要归一致。”雅是生活在凡尘世俗中的文人,以丰富的学识来净化心灵,完善自身品格,从而发自内心的一种超凡脱俗的高尚的人文涵养。
沈春泽说:“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正是这种真才、真韵、真情在家具制作中的注入,才使得明式家具具有了“有度”, “有式”,“精而便”,“简而裁”,“巧而自然”的文化气质。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些古代文人喜爱备至的、蕴含了文人思想的明式家具,之所以长久的耐人寻 味,让人爱不择手,正是因为这高尚而不平庸的趣味——“雅”的所在。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明式家具成为一种载体,表现文人的内心世界,消遣他们的人生情怀,余韵所及,渐成社会风尚。一种自古而来的返璞趋素的审美理念和艺术价值观逐渐成为全民族的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在明式家具上体现出的这种雅俗同流的社会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在明清文学作品中多有所反映。举世闻名的世情章回小说《金瓶梅》第二十五回有诗云:“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雪隐鹭鸶”这个意象,很容易让我们体味到平常的人情世态中所隐藏的深险湍流,让我们想起《红楼梦》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苍劲悲凉,或许还会让我们联想到在晚明思想和文学界极为流行的“空”和“无”。当然,《金瓶梅》所强调的“空无”,绝非空无一物,它一直在引诱我们去索解隐秘,探幽访胜,雅俗合流的季明文化风景、社会万象,以期达到“始见”和“方知”的化境。
作为中国第一部以“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创作的世情小说,《金瓶梅》对明代社会的市井生活、经济和物价状况的描述非常之多,被称为中国十六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其不同凡俗之处,却在于归于凡俗、世俗。其直面最卑微低贱的底层社会之世情,描写极淫亵鄙陋的市井小人之状态,使得中国传统文学从对王侯将相世界的艳羡回归到对小人物的命运的关注,从救民于倒悬的高尚回归到男女性爱的俗艳,“不再刻意追求‘温柔敦厚’,而是开始怀疑‘温柔敦厚’,不必再是优美、宁静、和谐、深沉、冲淡、平远,而是不避甚至追求上述种种‘惊’、‘俗’、‘艳’、‘骇’等等。” 看似惊世骇俗,“而在当时,实亦时尚”。(鲁迅语)
王世襄先生在《锦灰堆》一书中引用明代范叔子所撰《云间据目抄》中的家具条目,作为硬木家具在明代流行的例证,读来颇为有趣,从中我们不难窥见明代普罗大众对才子文化“雅致”生活方式的热情追捧:“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纨袴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极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者,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金瓶梅》曾长期背负放纵情欲文学恶名,然而,平心而论,它跳出传统文学历史和传奇的窠臼,抛却英雄主义和宏大叙事,我们也不难找到饮食男女这种对“雅致”生活的热情。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女含恨戳舌》里,应伯爵引着韩道国去见西门庆:进入仪门,转过大厅,由鹿顶钻山进去,就是花园角门。抹过木香棚,两边松墙,松墙里面三间小卷棚,名唤翡翠轩,乃西门庆夏月纳凉之所。前后帘栊掩映,四面花竹阴森,周围摆设珍禽异兽,瑶草琪花,各极其盛。里面一明两暗书房,……二人掀开帘子进入明间内……上下放着六把云南玛瑙、漆减金钉藤丝甸矮矮东坡椅儿,两边挂四轴天青衢花绫裱白绫边名人的山水,一边一张螳螂蜻蜒脚、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桌儿上安放古铜炉、流金仙鹤,正面悬着“翡翠轩”三字。左右粉笺吊屏上写着一联:“风静槐阴清院宇,日长香篆散帘栊。”伯爵走到里边书房内,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钿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这是《金瓶梅词话》里对西门庆书房“翡翠轩”的描写。翡翠轩在《金瓶梅》中不只一次提到,在三十四回中的这一节里,则是着意描写了轩中的位置和室内的陈设,其中对花园的描绘可以说是明代花园常见的布局。明人画作对此也常有细致的描绘,如沈周为吴宽所绘《东庄图》中的《耕息轩》,如钱榖为张凤翼作《求志园图》,如《仇文合壁西厢会真记》中的“红娘请宴”一幅。 书房里的东坡椅,其实就是交椅,《明式家具珍赏》中著录的一件可以为例。一封书大理石心璧画的帮桌儿,乃长方形的短桌,多用于供桌,在《明式家具研究》中亦可以找出一例,可见其式。
另一间“书房”是其当时江南一名妓所用,见诸明代冯梦龙所著《喻世明言》:明窗净几,竹榻茶垆。床间挂一张名琴,壁上悬一幅古画。香风不散,宝炉中常爇沉檀;清风逼人,花瓶内频添新水。万卷图书供赏玩,一枰棋局佐欢娱。名琴、古画、宝炉、沉檀、万卷图书、一枰棋局,这是何等斯文的书房。商人西门庆和妓女有书房,我们一直以为书房是画家、文学家们的专属。此乃大雅与大俗合流又一实证也。
关于明代文人书室雅斋内部的室内陈设,在明代流传下来的一些言情小说的文字描写中,也多有描绘。
明末方汝浩编著的社会言情小说《禅真逸室》一书中就记载在妙香寺的一处房间里,陈设有包括紫檀在内的多种家具。该书第七回记载:“赵婆引路,一同进去。转弯抹角,都是重门小壁,足过了六七进房子,方引入一间小房里。黎赛玉仔细看时,四围尽是鸳鸯板壁,退光黑漆的门扇,门口放一架铁力木嵌太湖石的屏风,正面挂一幅名人山水,侧边挂着四轴行书草字。屏风里一张金漆桌子,堆着经卷书籍,文房四宝、图书册页、多般玩器。左边傍壁,摆着一带藤穿嵌大理石背的一字交椅。右边铺着一张水磨紫檀万字凉床,铺陈齐整,挂一顶月白色轻罗帐幔,金帐钩桃红帐须。侧首挂着一张七弦古琴,琴边又斜悬着几枝箫管,一口宝剑。上面放着一张雕花描金供桌,侍奉一尊渗金的达摩祖师。”这段描述为今人了解明代居室内部的家具陈设情况提供了详实的佐证。这间房子里陈设有金漆桌子,在桌子上堆着经卷典籍、文房四宝、七弦古琴等,还有一张交椅以及紫檀万字凉床,在门口处摆放着一架铁力木嵌太湖石的屏风,相当典雅别致,颇具文人气息,算得上是比较典型的明代文人的家居陈设。总体而观,明代文人书房装饰简素,室内家具陈设无多,充满着“翰墨飘香”的书卷气息,体现了明代文人“心如朗月连天净,性似寒潭彻底清”的精神境界。
在揭露魏忠贤发迹史的小说《梼杌闲评》里描写兵部贪官崔呈秀豪宅里的陈设,也有大量篇幅讲到书房陈设,如《梼杌闲评》第四十八回《转司马少华纳赂、贬凤阳臣恶投环》里写道:“文梓雕梁,花梨裁槛。绿窗紧密,层层又障珠帘;素壁泥封,处处更绣白巇。云母屏晶光夺目,大理榻皎洁宜人。紫檀架上,列许多诗文子史,果然十万牙签;沉香案头,摆几件钟瓶彝,尽是千年古物。”书中讲到崔呈秀宅中的书房有云母屏风、大理石榻,沉香大案,还有紫檀架。其中,文中所描写的这件“列许多诗文子史,果然十万牙签”的紫檀架,其实就是一种专为盛放文玩书籍的架格,这种架格在传世于今的明式家具中多有出现,它是明代文人书房中必不可少的陈设,既可陈列书籍、卷帙,亦可展列珍玩。这个贪官的豪阔硬木家具可见一斑。
正如德塞图所说:“一个社会是由一定的实践来构成”,要了解这个社会的运行,了解这个社会的人群,就要理解这个社会的生活实践。由饮食、游艺、娱乐、交友、家具等构成的日常生活实践,构成了一个丰富的社会空间,任何一个巨大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一定起始于细微之事。于这些日常生活细节的勾勒中,我们可以看出明朝社会形态、文化品位,这正是探查明清古典名著、笔记小说中的传统家具日常生活场域的重大意义。
《金瓶梅》前言有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鲁迅对金瓶梅有如此评论: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总之是说,也就是那时候的小说,没有比它更好的了之意。我们翻开这本书,仿佛看到了一幅广阔的世态民情画卷。世人崇尚游艺,放纵情欲,追求享乐,违背礼制。。。打双陆、荡秋千、赏花灯、猜谜、下棋、跳百索、斗百草、行令、斗鸡等技艺,不仅表现了民俗活动的精彩和繁荣,而且折射出时代的审美趣味及社会风尚。无论是贫苦百姓捉襟见肘的生活,还是富商大贾纸醉金迷的享受,都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
“日常生活”作为一个研究范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就已经获得了重视。马克思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由吃喝、生殖、居住、修饰等组成的日常生活,在马克思理论中是支撑和实现其他社会活动的基础,使得“现实日常生活”在哲学领域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地位。
《金瓶梅》的故事时间背景虽然是北宋,西门庆也是北人,是明代小说家兰陵笑笑生在隆庆至万历年间所作。《金瓶梅词话》则是《金瓶梅》最早的版本系统,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东吴弄珠客及欣欣子作序。文学作品历来有借古喻今的传统,书中西门庆原型其实非“北宋西门庆”而是“明代西门庆”,里面描绘的书房也应是“明代的西门庆书房”。这种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手法在明代艺术作品中俯拾皆是。比如,汉宫春晓是中国人物画的传统题材,主要描绘宫中缤妃生活,而明代画家仇英的《汉宫春晓图》中,人物、发型、服装皆为汉代式样,但宫室、家具却皆是明朝的形制。因此,我们可以从皂快居止和西门庆书房里面的陈设管窥明代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而从其书箧内放“账簿”的做派,则形象地反映出明代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明代工商阶层经济上的崛起以及他们在文化生活上热衷于附庸风雅的潮流,从中我们也可以一窥明式家具诞生之初的深层社会历史背景。
明代文人的危机,从燕闲清赏到失意焦虑 。滥觞于宋代的文房雅玩是中国传统文化繁荣丰盛的佐证和剪影,而明代中晚期则是其发展的一个高潮阶段,这其中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所谓学而优则仕,文人群体通过学习和掌握圣贤知识,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便可进入仕途,从政为官。这使得文人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赋予某种特殊性以便与其他群体相区别,由此相应产生的价值体系便形成他们对文人主体身份的建构和自我身份的确定与认同。据统计,明代文玩共有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字画、花插以及香茶纸墨等共45种之多,这些高度艺术化的物品代表了中国文化艺术的最高水准,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外延,传递出精致、古雅、闲隐的生活态度。从中,我们可以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燕闲清赏之态。
然而,这种燕闲清赏之态到明代中晚期遭到了来自社会新兴阶层的强力挑战,并由清赏逐步变成了焦虑。石守谦在《雅俗的焦虑》一文中说:“中国社会自11世纪起文人文化便已逐渐成形,到了16世纪它大致上已经发展至独立自觉而成体系的状况。”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文人士大夫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不仅追求区别之势日益,而且拒绝被同化的焦虑亦日剧”,这种焦虑到明代中晚期更达到了极致。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明一代堪称黑暗时代。一方面,朱元璋及其后续者,为了维护其帝王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特务治国,对异端思想残酷压制,对有个性的文人大开杀戒。正如樊树志《明代文人的命运》一书所揭示:“士大夫面临两难的选择,刚直不阿,是为当道所不容;曲学阿世,则为后世所不齿……”另一方面,科举之途壅塞。据顾炎武估计,明末全国生员有50万人,而明初不过3~6万。但科考录取率却不断下降,以乡试为例,嘉靖以后降至4%以下,这意味着有60%~70%的生员只能以此身份终其一生。而在元末,江南一带是与朱元璋争夺天下的张士诚的占据地,因此明代中央政府对江南人士更天然地充满了疑虑与不信任,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江南文人在政治上的失意。

缘于中国自古以来的尚儒观念的影响,士居于“四民”之首,明代的文人在精神上也保留了中国传统文人“清高”“孤傲”的气质, “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随着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人们的日常生活愈加依赖市场和商品流通,对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开始淡薄,文人放低身段融入现实生活,“轻商”意识发生转变。同时许多民间的手工匠人“挟其技以游四方,名人胜流,竞相延结”,这也促使文人开始与匠人合作,甚至尝试亲自设计制作产品。一边是江南文人政治上的失意,另一边则是工商阶层在经济上的强势崛起。明朝中叶以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遥遥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一带是全国的财富重地,仅苏州一地,其税粮总额即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商人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强烈冲击了士人原有的“四民之首”的优越地位,清代沈垚在《落帆楼文集》中写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亦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正如费孝通在《皇权与绅权》一文中指出,明代四民的社会构成发生变化,“士而贾行”或“贾而士行”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明清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便发生在这两大阶层的升降分合上面”。
“四民相混”的社会现实让文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前所未有的,也动摇了他们固守的“重义轻利”的生存理念。再加上生计日益维艰、社会上文化消费需求的增强,“以本业治生”就成为士人一条重要的生活途径。提起唐寅,或许多数人会想起“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雅事,这颇为唐才子增加了传奇色彩。然而,与传闻不同的是,唐寅一生坎坷、命途多舛,人生和仕途皆不顺畅,或许反而成就了他的艺术辉煌。同时,当时发达的江南商品经济,也为唐寅参与艺术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中说唐伯虎“晚年寡出,常坐临街小楼,唯乞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虽任适诞放,而一毫无所苟”。这里的临街小楼,是唐寅在阜桥开店的老屋,说明他经常在此卖画。

事实上,卖文鬻画并非唐伯虎所独有,如明代大才子“忍饥月下独徘徊”“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徐渭“人操金请书文书绘者,值其稍裕,即百方不得,遇窘时乃肯为之。所受物人人题识,必偿己乃以给费”。记得第一次看到徐渭的《墨葡萄图》,那是一种什么心里感受呢?如黑云翻墨,如雨溅雹飞,如空谷长啸,如暮鼓急声,这已经不是在看画,分明是一个桀骜不驯的老秀才纵横泼洒着他内心的狂野、激愤和无尽的落寞。画外,一个厚重的旁白挥洒着墨叶间肆意狂舞的题诗:“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政治上失意的文人寄情于艺术创作,与经济上成功的商人生活中附庸风雅,促使二者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种意味深长、心照不宣的既尴尬又合作的关系。
(待续…….)
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24741756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