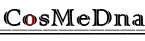本故事已由作者:直木,授权每天读点故事app独家发布,旗下关联账号“深夜有情”获得合法转授权发布,侵权必究。
1
御前公公已去半晌,东流仍伏首堂下,身子一动不动。尉迟烈回府时见到只当她睡着了。但她没有。
值深秋,青石地板凉得彻骨。东流在楚疆一战受了腿伤,见着寒气便疼得不能自已。尉迟烈又心疼又愤恨地去扶她,适时东流已自行起身。
她神色淡淡的,眸子空洞无神,看着外面簌簌落的木叶问道:“起风了么?”
说着话,衣裙下的双腿悄悄软了一下,却没能逃过尉迟烈的眼睛。他扶住她,想训她可不忍心:“你还是将祛痕膏给他了。”
他见着她眉尾长如蜈蚣般丑陋的疤痕,叹道:“当初为了祛疤,你忍痛往天山采药,九死一生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东流,仅一个娇弱的伊兰公主便教你败得一塌糊涂,当年那股战场上的狠劲去哪了?”
东流否定他道:“不是伊兰公主,是李承邺。”
爱上一个人,是最容易被击败的。
风大了,东流身子一寒道:“哥,送我回去吧。”
尉迟烈恨铁不成钢,但还是抱着她往回走。
东流昏昏沉沉,稍顷只觉颠簸忽然住了。疑惑抬头,只见尉迟烈满眼压抑的怒火直视着前方,而抱着她的力道不自觉大了一分,弄得东流身子一疼。
东流随他看去,只见李承邺一身玄色便装站在三丈之外的桐木下,眸子清冷正望向这边。心里忽然难受起来,东流挣扎着从尉迟烈身上下来,勉强行了一礼,却是不说话。
蒋太医把祛痕膏将将制好,伊兰公主便被茶水烫伤了玉指。等祛痕膏被送到了东流手里,御前公公便来尉迟府讨要。憎也好,怨也罢,东流爽快地给了。而今始作俑者站在她面前,她却像个做错事的人,除了沉默竟不知如何才好。
尉迟烈率先打破了僵局:“不知皇上驾临……”
“虚礼便免了,”在尉迟烈面前站定,李承邺走近说道,“令妹舍己救上,本该伊兰亲自登门拜谢,奈何有伤在身,只得朕亲临了。”
尉迟烈微微笑:“陛下言重了。即便要道谢,却也不该对臣下。”
说着,尉迟烈担忧地看了东流一眼,行了告退礼便去了。
风更大了。
凉风中,帝王看佳人,看杀春花与秋月。
东流垂眸立着,他不言,她亦不语。
李承邺先开的口:“楚疆之战回来匆匆见了你一面,半年了,你依然没变。”
“变”有多重含义。从小到大,东流都不曾看透他,眼下自然也不知他言的是哪重意思。
东流抬眸看他,随心道:“变了。”
她轻抚眉尾被刀刃划出来的疤痕,进一步道:“那时见你伤口还是渗着血的。现在,呵,连我自己见了都怕。”
微微一顿,她继续道:“跟伤口一起变的兴许还有心吧。”
李承邺瞬间怔了一下,重新嗫笑:“你总算长大了。”
总算长大了,知道了什么该爱,什么不该爱。
东流反哂笑,指了指眉尾,又指了指心口:“长大又如何?又忘不了你。原来只是爱在口,现在却像伤口,在心上不停结痂,一层又一层。我问过蒋太医,他说这儿的疤犹可治,但这儿的疤,生刻骨铭心,死带进坟墓。”
李承邺看着她,眸子如水洗一般,外表波澜不惊,清澈透明,却如何也令人猜不透他心思。大约看得入迷了,他不禁轻轻去碰她,却被她慌张地躲开了。
李承邺收回手,悻悻然,笑道:“不碍事,依旧倾国倾城。”
东流轻轻自嘲:“却倾不了你的心,对么?”
李承邺神色顿时僵硬了一瞬,须臾恢复了常色。
月光虽浅,但到底逃不过东流的眼。
“我知道了。”她道。
李承邺唇角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东流微微屈身又行一礼,艰难地抬腿意欲离去。
走至拐角,忽然撑不住地扶着柱子大口喘息起来。东流怕他看到,又期待他看到,回头只见他仍在原地,肯定是看到了。可是,他没有上前,没有慰问,只是站在她身后的夜色里,瞧不清神色,像个局外人。
2
蒋太医来给东流看腿疾时,谈起一桩往事,不禁跟东流打趣尉迟烈是个“戏痴”。东流笑了两声,忽然蹙眉:“哥哥是戏痴,妹妹是情痴,果然都是尉迟家的人。”
当日,她入宫去寻太后。
血缘上说,太后是东流三代以外的远房表姨母,所以,长这么大东流难得求她一次,她也答应得爽快。于是,次日,德勤殿便无端多了名没品级的御前带刀侍卫。
已入冬,天气干燥得紧。李承邺批了两个时辰的奏折,只觉得头昏脑胀,便命人点上龙涎香。这时,东流走了进来。
她束发加冠,穿着侍卫装,乍一看颇像那么回事。正自鸣得意呢,李承邺已搁笔走至她面前,叹道:“那晚,朕以为你已想得清楚明白。”
东流一怔,拿着火折子的手忽然就抖了一下。火焰一斜,正烧着指尖。她慌张丢了,把手背在身后暗暗咬牙忍痛。
“是已想得明白,所以才不肯轻弃。”她道。
李承邺脸色渐阴,道:“你在朕这没有结果,这般耗着,只是蹉跎光阴。哪怕太后允你在此胡闹,但明年选妃,你身有伤痕,即便是有太后的庇佑,你也没机会。”
东流眸子一涩,喉咙一酸,咬牙半晌终究咽了下去。
六年前采选,她求父亲送她入宫选妃,父亲不许,只道:“你左右不过豆蔻年华,入宫尚早。”
待她十五岁时,她又求父亲,但这次父亲已经拦不住她了。
是李承邺——她夜闯养心殿,顾不得他已更衣睡下,只求他下旨让父亲送她入宫。李承邺本该罚她的,但没有,单是问她:“你心中有什么?”
东流不假思索回答:“有你。”
李承邺愣了半晌,东流忘了后来他是何神情。只记得记事以来,他对她第一次声寒入骨:“可朕的心中是天下,已无多余空处安放儿女私情,更容不下你。”
那年选妃之后,南楚与西疆交战,尉迟将军为主帅,尉迟烈为副帅,二人率军直捣西疆。此役本无东流的事,就因他的这句话,她连夜喝马西欲去马革裹尸。
楚疆之战大捷。
东流想,她立了战功,回京李承邺多少会同意的,哪怕脸上受了伤,不过有神医蒋太医在,也不妨事。可是,错了,一切都错了。
西疆求和,送了伊兰公主入京,李承邺对其一眼千年。
她心底自问,不是已无多余处安放儿女私情了吗?
而现下……
“你是故意的吗?”东流问道。
李承邺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神色清冷:“是你一直执迷不悟。”
方咽下去的泪又不安分了,东流强忍道:“怪我么?”
她转头看向天际道:“你既看不上我,在我懵懂那些年,又何必以对待后宫娘娘那般对我,徒让我误会?”
李承邺表情微软,眸子也温柔起来,看着东流消瘦矮小的身子,竟然觉得喉咙发紧得厉害。
他忽然柔了语气,恍若当年:“到底你曾唤朕一声皇帝哥哥,对你好是朕应该。只是不曾顾及男女有别,是朕的错。日后你想要什么,朕必将满足。”
东流看向他,字字铿锵:“我只想要你罢了。”
李承邺脸色阴沉下来,想斥她。适逢伊兰携宫人进来了,听她吟吟笑着请安。
李承邺瞬即换了脸色,绕过东流去扶伊兰,假嗔怪道:“天寒地冻,不好好待在暖房里,吹这冷风作甚?”
伊兰当即娇嗔着伏在李承邺怀里,也不管四周的旁人。两人打情骂俏了会儿,李承邺这才责她注意形象。
东流依旧在原处,心里不知是何滋味。她只觉累得很,比在战场厮杀还要累,大约是怒的、气的,转头即走。不料没走成,被伊兰拦住了。
伊兰装作关切:“前些日子多亏了千金的祛痕膏,本宫的手才康好。只是不曾想千金眉尾的疤痕竟是这般骇人。若是早知,定会阻拦陛下的。”
她不言还好,一说,四周的宫人纷纷将视线聚焦在她那道蜈蚣疤痕上。一时,各都交换眼神此,蚊声交谈。
李承邺,只见他拥紧了伊兰,冷声呵斥。大约是在喝斥宫人,又或许是喝斥伊兰。东流已无谓了。
东流至逃走,他都不看她一眼。大约他也害怕她眉尾的那只蜈蚣。
3
东流住在了太后那儿。
期间李承邺来过,一则是请安,二则上次东流被火折子烧伤了手指,他来送些药看看,顺便差人打了三只不同大小的桐花花钿给送了过来,说是贴在疤上做装饰的。
东流当即便贴上了,金色的,太阳一照闪闪发光,煞是好看。
适时,不知谁低低说了句:“这回子皇上总算不用对着那道骇人的虫豸了。”东流心中一涩——他果然是厌恶那道疤的。
后来,尉迟烈受母命接她回府,东流不同意。盯着涂了药的手指,抚着眉尾的三只花钿发呆,嘴巴一张一合:“我放不下他。他对我不算坏,哪怕仅是作为兄长。”
尉迟烈气急,直骂她没出息,哪像个尉迟家的女儿。
除夕,东流领了太后的压岁钱后,便找不着李承邺了。她挨个宫殿去寻,后来在御书房找到了独酌的他。
他眉峰聚拢,整张脸溺在昏暗的灯光中,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落寞怅然。
东流不知他为何落寞,她看不透他。
她蹑手蹑脚地绕到他身后,本想捉弄他,却一个猝不及防被他环着腰圈在了怀里。东流错愕地仰看他,只见他两颊酡红,满口酒气,平日熠亮的双眸此刻似蒙了层轻纱。
——他醉了。
东流任他抱着,莞尔一笑,双手悄悄地攀上了他的颈。
他真的醉了,双眸迷离地看着怀中人,灿若桃花地露齿笑,手指温柔地抚弄着东流樱红的仰月唇瓣,意欲吻上去。
她等着他靠近,两寸、一寸……
他忽然停下了,柔情蜜意地唤了声:“伊兰”。
东流浑身一震,脸慌张逃开,两瓣薄凉柔软的唇便如烙铁一般焦灼在她的耳畔。这长夜真是冷啊。
东流艰难地呼出一口雾气,环着李承邺颈的手便松了。拨开他的手臂从他怀里出来,李承邺却拉着她的袖不肯松手,只一声声地呼喊“伊兰”。
方才那一声,东流只是胸口窒了一下。而现下,她直觉得胸口的那颗心裸露在外边,任凭他言语如刀,一下下凌迟。
他每叫一声,她那颗裸露的心便被生生剜掉一片肉。
李承邺的手拽得很紧,东流盯着那只手臂眸眼泛红。她咬了咬牙,对着他的手臂狠狠咬了一口。直到嘴里泛着腥甜,她才作罢。俱一仰眸,李承邺眉峰紧锁着凝视她,眼里带着猩红,仿佛一只发怒的野兽。
“咬够了?”他沉声问道,仿佛醉意已消大半,又或者他根本不曾醉酒。
东流不再看他,起身道:“咬够了。”对方才事只字不提,转身离开,却被李承邺一声吓住。
东流以为他会训斥,不想他叹了口气,蓦地放软口气:“尉迟将军近来身体抱恙。你已离家两月,该回去看看了。”
他离座至她面前,接续道:“这枚羊脂白玉可通行皇宫内院,权当做是朕给你的新年礼物罢。”
“多谢皇上恩赐,臣女恐用不着。”
李承邺知她不需要,但仍塞到了她手里,长长叹道:“毕竟你唤我一声兄长。”
话音刚落,伊兰的娇笑声已从殿外飘了进来。
是夜,东流便随尉迟烈归去将军府。尉迟将军康健得很,东流请个安便回了房。
次日早起拜年,父亲喜气洋洋地拿了幅画给她看,问她:“此人如何?”
东流懒懒扫了一眼,画中男子她认得。是去年的新科状元郎,徐尚书家的公子。
“玉树临风。”东流眼皮跳了跳,捂着发闷的胸口道。
话音甫落,宣旨内官便来了。
果然不是好事。
皇上赐婚东流,令禁足在府三月好生学习女红。
尉迟烈看管她极严,东流内功不敌他,私自出府几次都被抓了回来。直到入夏时,下了场暴雨,她的腿疾复发,趁着尉迟烈请太医的档子才偷偷跑出来。
见到李承邺时,他方从伊兰那殿回来。东流站在御书房内,全身湿透,嘴唇冻得青紫,看着他眸光里粘合了怨愤与悲戚。
李承邺原本略显苍白的脸色霎那不见天日。他屏退众人。
“你那双腿是不想要了吗?”他怫然道。
东流双腿疼得发抖,胸口亦疼的仿佛被人撕开,双眸如炬地直视他:“若是真的要我下嫁给尚书之子,莫说这双腿,命我都可以不要。”
尉迟烈骂得对,她实在是没出息。明明李承邺已伤她千疮百口,她却还爱他如初,简直不可救药!
李承邺冷笑道:“抗旨?你有几个脑袋?尉迟一府又有多少脑袋?”
东流愣了愣,太多的无力之感涌上全身,顿觉泪意席卷。
她强忍着酸涩,跪在殿下伏首颤声道:“不关他们的事,是我一意孤行,我愿承下所有的忤逆与不孝。”
京城那场雨连下了三日。
东流被尉迟烈带回府时,她已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蒋太医忙活了个把月,她才恢复意识,一醒来便抱着尉迟夫人嚎哭。
这一月,她一直徘徊在现实与梦境之间,耳边一直回响晕厥前,他薄凉如秋风的声调:“卿本佳人,奈何朕非良人。”
最后尉迟烈来了,带了封信给她。上书:“将你从前予我心,付予他人可?”
东流心中一疼,抬起哭得通红的眸子看向尉迟烈:“他可还有说什么?”
尉迟烈担心地看她一眼,缓缓吐字:“天长日久,好自为之。”
4
东流身子好转已是大雪。彼时太后已薨世两月余,李承邺伤心过度,抑郁气结,几度昏厥于朝堂之上。东流闻听,他已小半月未上朝了。
她到底存留着一丝执念,便借着还玉的名头前去探望。
他果真病了,躺在龙榻上,脸色骇人的白。见到东流,他先是一愣,等东流走近了,这才温润地笑起来。
他问道:“数月不见,你可还好?”
东流眼睛一热,背过身去道:“不好。”
蒋太医开了药方回来了,见东流佯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心中微恸。
“你过得这样差,我怎会过得好?”东流红着眼睛重新看他,疑问,“伊兰公主呢?”
李承邺掩唇轻咳一声:“她已守了朕数日,朕遣她回去歇息了。”
东流点了点头,随后咬咬牙,终究将玉佩还给他:“你既让我心托付给他人,以后,这宫闱重地,我不会再来了。”
李承邺嘴角的笑悠忽僵住了,随即笑地灿烂:“你终于是个大人了。既玉佩既已送出去,又岂有收回的道理?”
说着说着,他猝地狠狠咳起来。东流想上去给他顺气,却被蒋太医一把推开。她退出养心殿,怕打扰他诊治,在外面干站了一个时辰,终归等蒋太医出来了。
不等她问询,蒋太医已抢先一步唤道:“千金,恐怕方才的话要不作数了。这宫闱重地,以后还要多仰仗您的福音呢。”
东流回味一番,颇觉蹊跷,便随便捏个谎请他去府上。长谈至三更,尉迟烈方狐疑着送走他。奇的是,接下来东流开始闻鸡起舞苦练内功。
尉迟将军也是,自打陛下抱恙,便开始早出晚归。一直到来年春,李承邺身子终于好转。按照婚约,距离东流出阁只剩三月了。中间李承邺来过一次,听说东流练武摔伤了腿,加之旧疾复发,在榻上修养了一月。李承邺碰巧来找尉迟将军谈事,顺道慰问慰问她。
他进她的闺房时,东流正在打坐,见到李承邺,她胸口连跳了两下。
“你的身手已是京城数一数二,这还不够?居然要如此拼命?”他戏谑道,丝丝浅笑挂在略微病态白的面颊上。
东流看着他,反而有些释然,笑道:“总归有用的。”
闲谈了一日,李承邺回宫前叮嘱道:“已是待出阁的人了,以后便安静些吧。那些打啊杀的,不是你该管的,也管不了。只要朕在,你一世都可高枕无忧,明白吗?”
东流忽然不说话了。
李承邺欲走,她又忽然拦住他道:“你我已决绝,不必再对我这样好。”
他沉默了会儿,道:“朕与你断绝了关系,可是,你终究是朕的子民。”
东流正色:“我会忘了你的!”
李承邺转身去,浅浅一笑,凄凄切切,灿若星辰。
5
风起云涌。距离成亲还有小半个月,东流又见到了李承邺。
只是,此时非彼时。
尉迟将军勾结外敌欲行谋逆被当场拿获,尉迟府上下百十口人一夜之间悉数入狱。东流与尚书公子的婚约也解除了,她被锁在天牢九层,拿到圣旨的那霎,不知悲喜。
此宗案件彻查了两月,期间尉迟将军多次呈书明志,但指控与证据在前,任他百口莫辩,秋后被执行腰斩。
尉迟夫人闻讯,悲恸木然,一头撞墙而死。
尉迟烈本应革去功名爵位,放逐西北,却因出狱后以下犯上被乱箭射死。
至于东流,则贬为庶民驱逐出京。至此,尉迟一氏七代忠良,泯矣。
然而,不及驱逐,东流已急火攻心在牢内昏厥过去。
牢内湿潮,旧疾来势汹汹。她烧了许久许久,醒来已不知春秋。
瑟瑟风声,袅袅熏香。入目是一片模糊不清的昏暗,继而渐渐显现琼楼玉宇的轮廓。最后,李承邺的身影便如星火般撞进她眼眸深处。他绷着清冷的脸,眉间一抹浓愁,眼里似水温柔不断流出。一瞬间,东流以为是在做梦——哪怕只是一念温存,也没关系。
“真好,不枉我……”
——不枉我辛苦了这么些年。
她没说完,李承邺已变了脸色,冷哼道:“你倒是命大。”
旋身命令道:“罪人已醒,待恢复行动后立即驱逐。”
他走至蒋太医面前,呵责:“你救下罪人在先,私藏罪人在后,本该以死谢罪,念及蒋氏世代忠良……”
东流已顾不得他又说了些什么,胸口疼窒,全身酸痛,宛若经历了腰斩、万箭穿心般的劫难。这疼痛才使她真正醒转来,用一双噙血的眸子凉凉地看着李承邺,音色枯哑:“对不起,让陛下失望了。”
尉迟一氏基无幸免,将军府断壁残垣,她身后空无一人,怎么可以,怎么敢倒下?
东流在蒋府喝了数月的汤药。蒋太医怕她伤心萎靡,特意杜绝了府外一切消息。不过东流心眼玲珑,特意将李承邺给她的玉佩和伤疤处的花钿当着他的面投进了莲池,道:“我好得很,您莫担心我。”
她说这话时,声音柔软如春雨,眼神却像是眸子里镶了把剑,寒光四溢。见此,蒋太医竟莫明地信了她的话。东流也没骗他,至来年春,她恢复大半,已可以飞檐走壁,再运内功。
如此一来,被驱逐的日子便临近了。
走的前一晚,东流潜至池底又将玉佩与花钿寻了出来。乔装之后,凭着玉佩连夜入了皇宫。
已三更,李承邺还在御书房秉烛批奏。
东流低垂眼睑,端了壶酒进来。他依旧那么警觉,她近他两丈远,他便已经辨出她来。
“朕早就说过,没有演技与心计之人从不适合乔装。”他搁笔,抬首觑她。一双眸子爬满血丝写满疲倦,像是太久没歇息。
东流恍惚,肢体僵硬地将酒置于桌上。
李承邺执起一杯,环杯轻嗅,忽笑了笑,仰头饮下。
东流大惊,欲拦着,终究迟了一步。她夺去他手中玉樽,蓦然清笑,若风若雪:“毒酒入腹,却怕这穿肠毒药也不能让你体会何为剜心之痛。”
李承邺似早已知晓,面不改色:“是,你未曾下毒,朕自然体会不到。”
东流大惊,笑着笑着眼泪含不住,嗫嚅哭腔:“李承邺,你是何其残忍?”残忍到连她最后的尊严都践踏地体无完肤。
“你终是学不会恶。”李承邺道。
东流惶然惨笑,忍了这么多年,终于忍不住流下泪来。
“李承邺……”她温柔唤他,“这么多年,你未曾了解过我。”
话音甫落,李承邺只觉被银光晃了下眼,紧接着,便听见冷刃刺进血肉的声音。血汩汩流出,鲜红的、温热的,坠落在地上开出一朵朵绚丽的罂粟来。
他开始有了一丝痛楚,冷峻的容颜冒出细汗。
东流拧着眉,眸眼一眨不眨地把匕首拔出,仰首看着李承邺模糊的眉眼道:“这一刀,你不欠我了。”
她握紧了沾满鲜血的匕首,朝他胸口又狠刺一刀。四目相对,她泪眼婆娑,声如哀奏:“这一刀,李承邺,我不爱你,亦不恨你了。”
李承邺一动不动,甚至剑眉都未曾皱一下,唯有额头上不断往外渗的冷汗。一双疲累的眼盛满深情地看着她,嘴角噙着浅浅的笑,一副心满意足的模样。
东流却被这目光扎得如乱箭穿心般疼痛。她不知缘何生怒,面目狰狞如被惹急的兔子。她扔掉匕首,执起酒壶将玉露琼浆浇在他的伤口上,决绝道:“一杯祭我父母,一杯祭我兄长,一杯祭我执迷的过去。此后天高海阔,再不识君。”
她走了。似乎被人一早就下了命令,禁军者无一敢拦她去路。不足片刻,蒋太医便来了,像早已预知一般。
李承邺受了两刀,意识依旧清醒。见到蒋太医那会儿子咧嘴笑,笑得跟个孩子似的:“她终究学不会恶,这么多年,只有我最懂她。”
6
京城数月来雷雨磅礴不断。
李承邺在榻上度了数月时日。期间以伊兰公主为首的众嫔妃、以齐丞相为首的众朝臣都来过,皆被拒。一时间,朝廷上下不禁传道日薄西山,众人惶恐度日。
这日,暗卫递了份密奏进来。
值夏日,苍穹渲染,一碧万顷,是个好兆头。
李承邺道:“可以收网了。”
不消半日,伊兰公主与齐丞便便被押入天牢,罪名:勾结外敌,欲行谋逆。不日斩首。
彼时,南楚边界,尉迟父子已控制入侵中原的西疆兵马,现下正在押解回京的路上。
李承邺大喜,却倏地一口黑血咳出,奄奄待毙。蒋太医来看了,拿了数十味名药吊着,这才悠悠醒转。
蒋太医嘱咐道:“陛下日理万机,气血不畅,休养数日即可。”
李承邺坐起来,只觉心中有丝丝缕缕如针扎心的痛楚。他不安道:“朕昨日梦见东流了。”
蒋太医身躯一震。
他道,字字戳心:“她摆脱了朕派去暗中保护她的暗卫,偷偷潜入宫,只为了在朕面前自刎。血流了满地,染红枫叶,她笑自己一生执迷,眼睛装着恨,恨朕残忍,却至死都不愿伤朕一分一毫……”
蒋太医给他喂下安神汤,他才失去意识,沉沉睡去。半夜,东流来了。一身宫女装扮,想来是蒙混进来的。
“开始吧。”她道。暗暗看了李承邺一眼,心中不由得酸涩难忍。
蒋太医叹了口气,待东流躺至李承邺身旁,便用匕首划开了两人的手腕。
蒋太医掩送东流至京门外时,东流已气息奄奄。她再走不动了,只好扶着一棵柳树坐下,微微喘息着。
“我还有,多少时间?”她开口都成困难。
蒋太医回道:“不足半柱香。”
东流艰难地笑了笑,足够了。
她摆了摆手,蒋太医靠过来,耳附在她唇边,听她字字真情。
末了,微风拂过,天地寂然,再无声响。
再看,只见她双眸已阖,双臂已垂,靠着树干的身子不支,沉沉倒在地上。霎时,眼角溢出两行泪,匆匆滑进两鬓,只余两行清痕。
至死,她都不曾放下。蒋太医跪下给她磕了一个头,抬首,只见东方渐白。
李承邺醒来已是三日后。
蒋太医来复诊,不及入殿,便觉怒意四溅。进殿后果然,只见李承邺已下榻,药碗碎一地,奏折也撒了一地,其中夹杂着一封密信。蒋太医行礼时瞄了一眼,上写着:“罪人失踪。”
蒋太医不动声色,把脉之后便退了出来。走至玄关处,忽然见一人影像极了故人。他走上前去,微微颔首:“恕老朽唐突,公子神韵与老朽一位故人颇为相像,敢问公子何处高就?”
尉迟烈愣了半晌,终浅笑道:“不敢。不才晚辈郁无情,在御前任四品带刀侍卫,区区小官,不敢攀附。”
蒋太医大笑一番,告辞离去。
尉迟烈则轻叹一声,满目苍凉,进了养心殿。
“臣郁无情拜见皇上。”
7
蒋太医再次入宫时,李承邺与郁无情正在御花园长谈。
“她大约是恨朕的,所以才躲着。”
“那时,奸佞猖獗,后宫娘娘频频惨死,陛下那般待她,也是为了保护她,奈何她爱之入骨,不辨陛下深情,”郁无情顿了顿,又道:“假死一事,也怪臣当初不曾提醒她一二,才致她误会了陛下。”
李承邺惨笑:“说来说去到底是朕负了她。”
岁月静好,人去故去。李承邺寻了东流七年,后宫亦枯寂了七年。
清明,蒋太医给东流祭酒之后便倒下了,怕是大限将至。
李承邺来看他,他说不出话来,一双枯萎的眼紧盯着书架上的檀木奁,焦灼地张了几次口,便西归了。
李承邺狐疑地命人打开那奁盒,见到里面物什时,陡然木然。那是一枚玉佩,三枚桐花钿,底下还附了封信,打开看,是蒋太医的字迹。他对不起东流,瞒了那么多年终于瞒不住了。
当年他查出圣上中了西域奇毒,此毒乃慢性毒药,以处子之身为皿,通过肌肤之亲传染,中毒者无所知觉,虽表现为风寒之状却五年必丧。若解毒,只能以内功深厚的处子血与之换血,俗谓“以命换命”。
顾及朝堂局势,伊兰眼线众多,齐丞相虎视眈眈。不得已他才寻了东流商榷,她毫不容商量决定以命换命。
李承邺出来时,身子颤了一下,脸面潮湿。他问道:“是下雨了吗?”
内官回禀道:“启禀皇上,骄阳正当头。”
李承邺凄然扬起唇角,回宫后便大病了一场。
中秋既望,郁无情来看他,二人月下对酌。
“当年她多次相逼,我都显些要败给她。除夕那回装醉,我多想将错就错,可是不能,我给不了她安稳。”
他饮下一杯,辛辣入喉,快意肆然。
“这一世我身为帝王,不负天下人。唯东流一人,我负她太多,太多。最后一次见她,她说我不欠她了。可是,只一刀,怎么能还得完呢?”
“如有来世,我还是愿做个白衣鸿儒,不工心计,不屑权谋,只游山玩水,吟诗作赋,”他兀自笑,仿佛看到了来生,“当然,还有陪她。”
郁无情亦饮下一杯,本无意伤他,禁不住道:“恩怨纠葛,无非是春水东流。这一世,她生时伤痕累累,死后无名无碑。若是我,来生是如何都不愿见你的。”
李承邺又道:“可你不是她,她一定会的。”
月满西楼,红颜都成旧。
若是蒋太医还在,大约会同郁无情一样,反驳他一番。
无论多少年,蒋太医都怕清楚记得那晚,记得那晚的东流。
她说:“这一世是我的错。执拗一生,爱而不得,落得个满门惨死。今我年纪轻轻殒命,非是舍身为他,而是心率衰竭而死。只求我死后化骨扬灰,不立碑,不祭奠,不入轮回。”(原标题:《秋意浓》)
点击屏幕右上【关注】按钮,第一时间看更多精彩故事。
(此处已添加小程序,请到今日头条客户端查看)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1795171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