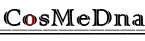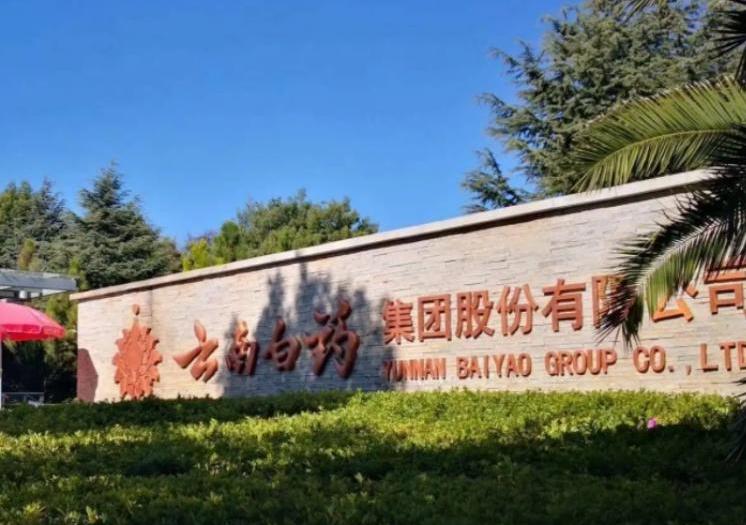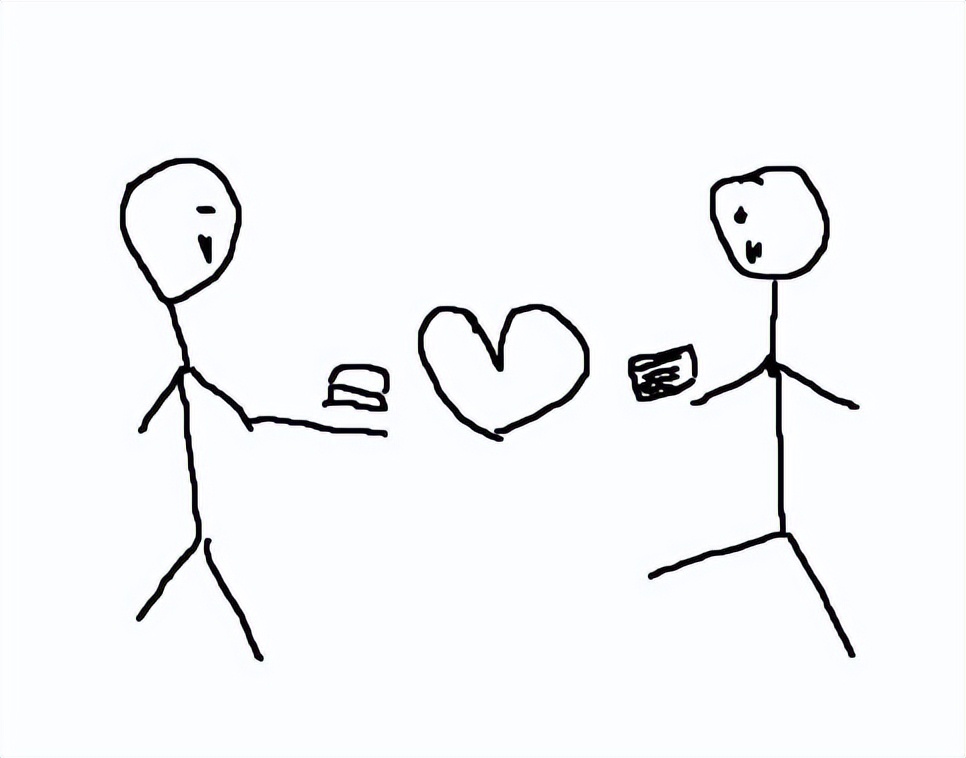什维亚在《作者与我》中探讨了作者、自我和书写三者的关系,它通过虚构故事模拟了几种自我虚构的情境,在每个情境中都有一个备受书写困扰的作者,这些虚拟作者们的微环境和现实中作者的书写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自我书写情境。作者通过多线的叙事层级消解了作者和自我的概念,试图通过重构语言再现自我。它向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现实和虚构的关系,作家和作品的关系,自我和叙事的关系。本文运用叙事学、传记和自我虚构等方面的理论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WW018),浙江省“钱江人才计划”C类项目(QJC1402006)。
作者简介:赵佳,浙江大学外语学院
在80年代以来法国文坛频繁出现的“自我虚构”(l'autofiction)的浪潮中,什维亚(Eric Chevillard)属于后来者。科罗那(Vincent Colonna)这样定义自我虚构:“如同在自传中一样,作家处于作品的中心(他是主人公),但他通过一个不真实的、无所谓相不相似的故事改变了自己的存在和身份。他的变体成为一个特殊的、纯粹虚构的主人公,没有人会想到从中得出作者的形象。和传记不同,自我虚构并不表现存在,它发明存在。现实和书写之间的距离毋庸置疑,不可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它是完完全全对自我的虚构”(75)。从2009年以来,什维亚才陆续有自我虚构的作品出现。四部明确以自我虚构为题的日记体作品(2009年出版的《自我虚构》[L' Autofictif journal,2007-2008],2010年出版的《自我虚构看到一只獭》[L' Autofictif voit une loutre journal,2008-2009],2011年出版的《自我虚构,父亲和儿子》[L' Autofictif père et fils journal,2009-2010],2012年出版的《自我虚构找了个教练》[L' Autofictif trouve un coach journal,2010-2011])发轫于什维亚在网络上开的博客,他将博客中的文章整理成集,便有了这些日记体的自我虚构。我们在作品中很难捕捉到作者真实自我的痕迹,题目中的自我更多具有反讽的意味。作者在第一部自我虚构的前言中说:“之所以冠名以自我虚构,一半是因为迷糊,一半是出于对自我虚构这一类型的嘲讽,长期以来我就不怀好意地对此加以嘲讽”(L' autofictif 7)。作者的嘲讽体现在自我的完全缺位。在什维亚的自我虚构中,自我是难以被圈定的,他时而是这个身份,时而是那个身份,时而在想象中,时而在梦境中,时而在互文中,却始终不在现实中。“我感到轮到自己像个人物了,我完全进入到我的虚构中,现实也在虚构中,可能也同样梦幻。我无所禁忌,这是原则”(L' autofictif 8)。
2012年出版的《作者与我》(L' Auteur et moi)是一部小说,书中频频出现什维亚的真实信息,再次模糊了真实和虚构间的距离。这部小说更像是此前《托马·彼拉斯特的遗作》(L' Oeuvre posthume de Thomas Pilaster)和《英勇小裁缝》(Le Vaillant petit tailleur)的混合体。它借用了《托马·彼拉斯特的遗作》的结构,采用正文和注解并行的双重叙事,正文的叙述者和注解的叙述者分开,形成两条不同的线。该小说还重现了《英勇小裁缝》的主题:作者如何通过自己塑造的人物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于是在正文和注解两条线外又出现了人物和作者两条线。四条线交叉进行造就了《作者与我》纷繁复杂的叙事结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该书秉承了什维亚一贯东拉西扯、枝节横生、插科打诨的风格。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什维亚所有作品中最考验作者叙事技巧和读者阅读水准的书,也是将反讽和怪诞推向极致的作品。
小说的题目《作者与我》指出了这部小说想要探讨的两个层面:作者和自我。既可以理解为作者的自我,也可以理解为自我的作者。作者既可以指什维亚自己,也可以指所有广义上的作者。而自我不仅是什维亚的自我,也是所有自我书写的中心——“我”。从这个意义上说,什维亚这部以虚构为名的作品比其他任何冠以自我虚构之名的自传作品更深刻地探讨了作者、自我和书写三者的关系,它通过虚构故事模拟了几种自我虚构的情境,在每个情境中都有一个备受书写困扰的作者,这些虚拟作者们的微环境和现实中作者的书写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上的自我书写情境。它向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现实和虚构的关系,作家和作品的关系,自我和叙事的关系。在下文中,我将以《作者与我》为例,从三个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多线的叙事层级,作者和自我的消解,书写和语言的再生成。
一、多线的叙事层级
这部小说有两条叙事线,一条是正文的叙述者,一条是注解的叙述者,我们将正文的叙述者称为叙述者一,将注解的叙述者称为叙述者二。从小说的“敬告读者”中可以看出,其实这两个叙述者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另一个叙述者的变体,我们姑且将这个叙述者称为“元叙述者”。原因有二:1.两个叙述者都源自于他的自我裂变;2.他对自我的呈现始终折射了文本的运行。“元叙述者”是一位作家,“敬告读者”可以看做是他的写作宣言。这位作家决定在接下来的篇章中“坚决地和他最新的小说中的叙述者拉开距离”(L' Auteur et moi,14),他的方式是“每次合适的情况下亲自介入,冷静地、坚决地避免任何混淆”(14)。
这个例子从一开始就区分了作者和叙述者的差别,而对这个差别的辨识在自我书写的文本中尤为重要。通过叙事学的发展,今天的文学评论已经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写书的作者和故事的叙述者并不是同一个人,热耐特(Genette)在《辞书三》(Figure Ⅲ)中指出:“一个虚构叙事的叙事情境永远都不能归结为书写情境”(226)。有时叙述者明确具有和作者不同的身份,有时叙述者的身份并不明确,并带有作者的痕迹,我们所探讨的自我书写属于后一种情况。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自我书写的作者和叙述者是同一的,自传理论家勒杰内(Philippe Lejeune)认为在自传体中,作者、叙述者、人物三者是同一的,“文本内部的发话主体和被言说对象指向叙述者和人物;发话主体通过自传体契约指向位于作品边缘的作者的名字”(Lejeune 39)。但叙事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不管两者再怎么相似,都不具有相同的地位。从自我书写的角度来说,文本中的“我”(也就是叙述者)是一个虚构的主体,而作者的“我”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这种“本体”上的差异带来了一系列后续视角上的差异。自我虚构的盛行凸显了自我书写中经常被混淆的两个主体的差异。什维亚的《作者与我》用有意为之的分裂生动地呈现了自我书写中“我”的双重性。
正文带有叙述者一的自传体痕迹,他围绕着一盘奶酪花菜絮絮叨叨,东拉西扯,漫无边际地展开各种话题,中间穿插了一些过往的生平。读者无从考证叙述者生平的真伪,通过叙述者二的评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正文可以看做是叙述者一的自我虚构。叙述者二的功能是运用注解对正文进行评论,他总是无情地指出叙述者一的自我书写和现实并不吻合的成分,指出叙述者一并非百分之百是作者的再现。他将作者和叙述者的差异定义为“作者”和“人物”的差异,也就是说叙述者一是作者所塑造的一个人物。但是叙述者二并不完全依附于叙述者一的叙事而存在,他有自己的独立性。如果说注解一开始只局限于揭露正文的幻觉,越往后注解越僭越了正文的地位,它自身变成了正文。叙述者二在注解中讲述了自己的过往,而这些过往明显带有虚构的性质。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叙述者二作为自我书写幻觉的揭露者,毫无顾忌地进行了自我虚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文和注解构成了两个自我虚构叙事,一方面明目张胆地进行自我虚构,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揭露自我虚构,给整个文本打上了什维亚特有的精神分裂的气质。这种分裂在《托马·彼拉斯特的遗作》中欲说还休,因为两个叙述者是两个不同的人,在《作者与我》中因为两者身份的统一而使矛盾愈加鲜明。
作家什维亚的加入使本书的自我书写更加复杂。“敬告读者”的“元叙述者”指向现实中的什维亚:比如《杀死尼扎尔》(Démolir Nisard),《迪诺·艾格》(Dino Egger),《死亡让我感冒》(Mourrir m' enrhume)均为什维亚的作品名称;文中引用了《没有猩猩》(Sans l' orangoutan)和《英勇小裁缝》中的句子;叙述者二以什维亚的小说《红耳朵》(Oreille rouge)为原型进行二度创作;“元叙述者”的风格和创作理念与什维亚如出一辙。当一切都将“元叙述者”指向什维亚本人时,小说在不同层面打破了两者的同一性:“元叙述者”在小说中虚构了很多关于什维亚的事实,使什维亚的真实性受到怀疑。什维亚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或是文本虚构出来的一个形象?这一疑问在小说最后达到了顶峰:叙述者一偷了一颗花菜,被发现后被众人追赶。一个叫什维亚的人出现,抓住叙述者进行搜查。如果说对什维亚的身份的影射在一开始制造了自我书写的幻觉,那么在最后将什维亚作为人物引入虚构中,并和叙述者对立起来的做法打破了两者的同一,直指自我虚构的本质。
多维的叙事层级会带来身份上的混淆和叙事上的越级(métalepse),“所有故事外的叙述者和读者进入故事内(或故事内的叙述者进入第二层故事内)或相反的情况[都可以被称为越级]”(Genette 244)。比如叙述者一和叙述者二讲述的不同故事中,两个人物之间因为奶酪花菜发生了身份上的混同;再如叙述者一和他创造的人物一起进行了一场真实的旅行;或者当“元叙述者”邀请读者翻到下一页时,小说也自动进入下一章,这个做法将虚构的文本和真实的文本混同起来,实际上是将叙述者和现实中的作者混同起来。这些不同做法不但在虚构内部实现了人物身份的混淆,也成功地模糊了虚构和现实间的界限。
二、消解“作者”与“我”
在一部带有自我虚构性质的作品中,什维亚将自我书写和作者形象的塑造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将“作者”和“我”并置在一起,什维亚将自我定位为一个作家,通过文本的进展来言说自我。“我”随着“作者”形象的建立而建立,随着“作者”形象的破坏而破坏。整部小说延续了《托马·彼拉斯特的遗作》中自我破坏和自我建构交替的主题。
作者形象的消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最主要的手段是文本的双重叙事:叙述者一企图建立作者的自我形象,而叙述者二则不断暗中破坏作者的自我书写。比如当叙述者一讲述了一件得意的事情,叙述者二便急忙对此事加以澄清,指出其谎言的性质,叙事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再比如对同一事件采取两种不同的视角,对作者自以为是的视角进行修正。叙述者二还经常使用戏仿的手法,模拟叙述者二的风格和观点,通过夸张的变形指出其风格的可笑和观点的荒谬。
消解作者的第二个方式是破坏作者作为文本主宰者的形象。首先间离作者和人物的关系。在经典小说中,作者是人物的创造者,人物妥帖地臣服于作者的控制,人物既是作者的工具,也是作者的表达。在什维亚的这部小说中,作者对人物始终怀有警惕的心理。在“敬告读者”中,作者一再和叙述者撇清关系,认为叙述者的立场并不能代替作者的立场,并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一再指出两者的差别。叙述者二说:“一个人物不受控制,如同一个暴露秘密的口误,如同一个不由自主的行为”(L' Auteur et moi 250)。人物如同作者的影子,暴露了作者的想法和情感。作者也许有意在叙事中掩盖自己的想法,但人物总会在不经意间揭开作者的面纱。作者对人物既抱有期待,又怀有警惕。什维亚这部小说中作者从一开始就希望和人物拉开关系,这份警觉不单是对叙事本身的警觉,也是作者对完全敞开自身的警觉。
除人物的不可控以外,还有叙事的不可控,这是消解作者的第三个方式。“元叙述者”在开场便说:“作者陷于虚构中,他被从桌子前拽起来,裹挟在从他平稳的手中迸射出来的词语流中,支离破碎,分崩离析,他紧紧地抓住他的句子,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他的木板”(15)。这段话预示了叙述者一的叙事,正文围绕着一颗奶酪花菜展开各种话题,随心所欲,东拉西扯,并无中心可言。这已经不是通常意义上有结构有内容的叙事,而是失去了重心的话语碎片所组成的洪流。叙述者二的虚构稍微增添了几分故事情节,但同样呈现出失控的趋势。它讲述了一个叫布雷兹(Blaise)的杀人犯在逃亡过程中遇到了一只蚂蚁,他跟随蚂蚁的踪迹前进。整个叙事如同主人公的路线无章可循。很难说究竟是汹涌的话语流造成了叙事方向的迷失,还是叙事方向的缺失造成了话语的决堤。总之,失去中心,连绵不绝的话语流和失去方向,被偶然性原则支配的叙事共同指向一个无力控制文本的作者形象。作者作为文本结构的组织者和文本意义的给予者,其地位受到了动摇。和一个巴尔扎克式的、自信的、权威的、上帝般的作者形象相反,读者所面对的是一个被废黜的、迷茫的、失去把控的黄昏中的偶像。
和作者形象一同被破坏的还有自我的形象。在一部自我书写的作品中,真诚是首要原则,任何虚构的举动都会打破文本中的“我”和现实中的“我”之间的同一性。当自我虚构不再被遮遮掩掩,而是直接地、招摇地出现在读者视野中时,它揭示了一个现象:自我的再现出现了转变。当代小说似乎很难再以直接、透明、回忆式的、感伤主义的方式再现自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间接的、有距离感的、若即若离的、片段式的自我言说方式。我们既看到对制造“现实主义幻觉”的回避,对任何“再现”的不信任,也看到精神分析对主体意识的分层,以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主体概念的排斥和消解(Viart 27-28)。萨洛特所说的“怀疑的时代”不仅是对小说幻觉的怀疑,也是对自我概念的全面怀疑。个人主义发展到近期进入“自恋”的阶段导致涌现了各种自我书写的文本,但这些文本透露出对自我的怀疑、戏谑、肢解和再拼接。“我”是文本所制造的一个视像,当视像被戳破时,后面什么都没有。《作者与我》走得更远,它提出了另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形象背后有“真实的我”存在吗?“真实的我”会不会也是一种幻觉?
叙述者一的自我虚构始终围绕着奶酪花菜进行,过往的零星片段间或出现。我们很难通过话语片段拼凑出一个完整的作者形象,唯一确定且重复出现的是花菜的形象。“我对花菜的厌恶成为我个性中唯一固定的点。[……]对我这个这么模糊、这么宽泛的人,我只能说那么多,只能理解那么多。我对花菜的厌恶成为坚实的、最不易碎的基础”(L' Auteur et moi 67-68)。花菜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所有关于自我的片段。它是信手拈来,并无根基,也无内涵的一个形象,它可被任何东西替代,如一条鱼,一个杏仁,一双鞋等。自我的所有根基建立在这个空洞的能指上,或者它所指的东西如它一般空洞,或者它并不指向任何可被命名的东西。前种情况说明自我本质的缺失,后种情况则揭示了自我的完全缺场。两者都勾勒了一个空洞的自我形象。“我”只存在于语言中,语言之外并无本体。关于自我的所有言说皆是语言围绕着一个缺席的所指的自我言说。在说到什维亚的书写时,朱尔德(Pierre Jourde)说:“这种书写制造我们所一直缺失的东西,我们的话语和文化花费大量时间来逃避,并让我们相信它们想让我们相信的这些不可言说的东西,这个客体本身是隐藏着的他者”,“好像我们每次都在接近一个不稳定的综合体,这种炼丹术的产物不可描述,只能通过无尽的曲折”(“Les Petits Mondes à l' envers d' Eric Chevillard” 213-14)。什维亚尖锐地指出主体概念不过是文明的产物。
作者的消解和自我的消解相辅相成。自我的消解对现实的感知提出疑问,作者的消解对再现的能力提出质疑。当对现实的感知成问题时,任何再现都是话语的自我重复。当再现的能力出问题时,自我的轮廓更加难以界定。现实的溃败和叙事的失效取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经验,“整个世界轰然坍塌。人们的信仰,形成的梦想,坚持的原则,一切都破败,出现裂缝,消解,一切都倒塌了。花儿和蝴蝶有什么用?太阳是什么?”(L' Auteur et moi 22)。我们看到了什维亚一以贯之的破坏者形象:破坏经验,破坏语言,破坏逻辑,破坏文明……世界在作家反讽的笑声中化为乌有。如何在灰烬中重新叙事,重拾自我?什维亚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三、走向何种语言?
什维亚的自我虚构导致对世界本身的质疑:现实是什么?该如何描述现实?叙述者认为我们所惯常认为的现实是我们的思维制造的效果,而真正的现实本身却在这种虚构的炮制中隐而不现。“我们的现实完全被语言所发明[……]并被经验所肯定[……]但经验是虚伪的,因为它也不过是一个事实或一种语言的效果。如果死亡是唯一的现实,那么只有它能够摆脱言语,而其余剩下的,包括我们在内,不过是虚构的作者和人物?”(47)。作者指出了现代文明重负下对现实的感知模式。我们身处一个由文字、图像和符号组成的世界中,满是对世界的再现和阐释。现代人自出生起就浸淫在这个符号的世界中,对现实的感知很多来源于对符号的感知,再现的世界反过来塑造了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方式。于是日常经验只不过一再验证了再现的世界。什维亚对我们身处的经验世界再次提出了本体论上的问题:经验是否真实?是否有效?是否和符号一样只是臆想的产物,并被语言的幻觉所笼罩?
除了被文化和经验所限定的现实,我们该如何找到生存的维度?什维亚将创造的希望寄托在语言上,但并非用语言去描述那个已经被限定的现实,而是用语言重新创造一个现实,“用语言对一个可能的生活进行肯定,这个生活超越了所有的偶然性和物理法则”(252)。语言是编制谎言和幻象的工具,但也是创造新现实的途径,它在经验的现实和理想的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在奶酪花菜和杏仁鳟鱼之间有一个世界,这是人类倾其所有所建立的一个世界,让它适于居住”(33)。这是人类赖以“诗意地栖居”的文字乌托邦,叙述者“天真地梦想被放逐在美丽的乌托邦世界里”(27)。如果说语言并不单纯是再现的工具,它是存在的物质性的一部分,那么如何找到一种适合的语言,只展现自己的物质性,即语词本身?通过寻找语言的物质性来通达存在,进而通达自我,成为这部小说,甚至什维亚所有小说的出发点。
叙述者所找到的语言也是作家什维亚所独有的语言。一种杂乱、异质、磅礴、多维度的语言;一种不断向前、急速滚动的语言;一种如洪水一样喷涌、不可遏制的语言;一种急促不安、妄图囊括一切片段的语言;一种“无尽的在流动中的散文”(136)。各种存在的片段随时涌来,成为漂浮的所指,它们很难被集中在一个方向,体现了生存的混沌状态。叙述者一的叙事更多是毫无关系的话语片段的填充,叙述者二的叙事则是逃亡的叙事,人物的逃亡,动物的逃亡,语言的逃亡,毫无方向,一个接一个,不断向前。作者企图用语词来填充时间,造成存在的绵延感,并在空间中并置所有琐碎的物象,构筑一个微小而全的世界。什维亚的语言同时用时间和空间搭建一个存在的舞台,创造一个微型的在生成中的宇宙。用这样的语言所书写的虚构已不再是对任何一种现实的再现,它本身成为存在的一部分。以语词的多维应对存在的多维,以语词的无所指来应对存在的无所依,用朱尔德的话来说,“以执行的速度为代价,我们可以通过重复言说来达到言说的强度,通过数量来达到质量。[……]在语词的多和重复中寻找存在的一”(Jourde,“L' anthume d' Eric Chevillard” 273)。我们无法确定语言最后会落在哪里,重要的是语言不断向前,不断凝聚所有的片段,让它们围绕在无意义的周围,如同奶酪花菜一样“吸收所有它所接触到的东西,直到分子的完全融合”(L' Auteur et moi 256)。正是在吸纳和向前的过程中,生存展现出它全部的实在性,并和语词的物质性合二为一。
但是,什维亚的语言不尽然是持续向前,它同时也是断裂的。叙述者二提出有两种断裂,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突然的。自然的断裂出现在具有现实主义幻觉的文学作品中,这些作品尽量构造一个符合现实和逻辑的世界,但并不代表没有断裂。叙事的断裂更多来自现实的断裂,而现实主义企图用幻觉来掩盖现实的断裂。还有一种文本是故意为之的断裂。这种断裂有一种“突然、倏忽的特征,使它更加容易被感觉到。断裂、破碎、持续性的消解”(189)。突然的断裂具有惊愕的效果,让我们看到原本看不到的实在。现实的幻觉被打破,存在的真相被推到面前,逼迫我们直视视而不见的断裂。《作者与我》全篇不分章,一气呵成,但是词语流所构成的假象并不能掩盖词和词之间的断裂。比如以下这段:“请说谋杀,因为你不知道枣这个词。因为呼啦这个词在你嘴里是个嗝。请说谋杀,正如你用你那昆虫的语言说的嗞嗞嗞。但是应该说快感,睡衣,丁香,咏叹调,机械或蔚蓝。应该最后一次说自行车”(42)。词语的叠加并不遵从任何逻辑,重要的是快,在语词落地生成意义之前被接住,一个接一个如分隔的珠子一样被串在一起。如此这般的断裂以迅猛的速度砸向读者的神经,语词的断裂扯开了断裂的现实。
以上这个例子不光是现实的断裂,同时体现了逻辑的断裂。什维亚在本书中继续声讨惯常的逻辑,破坏逻辑赖以存在的幻觉,即语言本身。叙述者在小说一开始便说:“为了引导和加快叙事,他打算进行谵妄的加速,他喜欢将逻辑的话语推向极致,因此远远超越了理性停止的地方,理性是如此智慧、谨慎、无聊、庸俗”(7)。在作者看来,打破逻辑的方法并不是故意建立某种非逻辑来和逻辑对立。什维亚在一篇访谈中说,“我并不放弃逻辑的方法,但我穷尽它。我掘取所有的后果和效果。但我稍稍一夸张,怪异的效果就产生了。这证明怪异已经隐含在逻辑所能到达的最初的解决方案中,我们的理性又顽强地对此进行重复。一切事情的荒诞性就是从如此的清醒中来的。任何事情都是荒诞的,因为只需要一点东西就使它变成别的”(“Ecrire pour contre attaquer” 330)。他顺从逻辑的思路,将它推向极致,逻辑突然调转了方向,暴露了自身的虚妄,成为自身的对立面。作者像拆解自我和现实一般,用同样自相矛盾的方法消解理性。重要的是速度,用快速的话语链堆积似是而非的逻辑。语言的非逻辑是为了言说存在的混沌。它只能抓住虚妄的不存在,却无法达到不在场的存在。于是,只剩下言说,自我本身归结为言说的动作。话语的物质性、言说的动作和存在三者融为一体,成为作者新的生命体验。
什维亚的语言最后还包含了反讽。反讽是什维亚喜欢的风格,是他的利器,也是他的身份。在《作者与我》中,叙述者二将叙述者一的一篇有关反讽的文章原封不动地抄了下来。在这篇文章中,叙述者一一再声称自己的文章没有半点反讽的意思。他例数反讽的种种罪状:卖弄智巧,道德上的懦弱,冷漠等等。叙述者说:“我的书中没有半点反讽。一切都打上了真实、真诚和情感的烙印。[……]当我说白色,就是指白色,当我说猫,就是指猫。[……]我希望所有的白纸黑字都只有字面上的意思”(L' Auteur et moi 245-43)。这里涉及反讽的双重语义:字面意义和实际意义。反讽者说的是一回事,表达的是另一回事。叙述者通过否认自己的语言具有双重含义来否认自己具有反讽的风格。读者明白叙述者在否定反讽的时候仍然在使用反讽的手法。什维亚的叙述者并不仅仅具有反讽的意图,他的语言更是打上了多重语义的烙印。“作者是硕果累累的多义女神的朋友”(251),叙述者在讲到奶酪花菜的意义时说。多义,因为语言难以进行一对一的表意,词语很多,意义却空缺。于是,所有的词语都想指向一个意义,但最后却什么都指向不了。多义,是存在的高度真实,却也是存在的无奈。作者既嘲讽了忠实的再现,指出词和物之间的完全对接是不可能的,又表达了统一词和意义的愿望。词语的乌托邦不单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言的理想世界,也应该是实现整一存在的途径。反讽不再是单纯的嘲讽或卖弄,而是表达了对透明存在的向往。“正是在同时无用但必要的对本体的永恒追问过程中产生了反讽”(Bessard-Banquy 253),旁吉如此评价什维亚的反讽艺术。
什维亚在《作者与我》中探讨了作者和自我、自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如同在什维亚很多其他同类题材的小说中一样,作家总是以自我分裂、似是而非的面目出现。与一个无法控制人物和叙事走向、深陷在词语流中的作者对应的是一个空洞的、分裂的、没有重心的自我形象。多线的叙事层级和多声的话语环境勾勒出一个由众多话语碎片拼贴成的自我,由此作者对主体的坚实、甚至是在场提出了质疑。作者和自我不再是可被辨识的主体,他们的消解导致对现实本身的怀疑:由经验和语言肯定的现实是否存在?它会不会只是一种话语效果?
本体论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家将其搁置起来,他不再执着地探讨在场与缺席、真实与虚妄的对立。他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语言物质性的延展中,通过建立语言的乌托邦来建立另一个生存维度。什维亚在《作者与我》中的语言如汹涌的洪水般喷涌而出,不断向前,裹挟着各种话语断片,围绕着一个空缺的意义不断言说。如此的语言不以再现为己任,不以逻辑为指向,只是单纯地言说。作者将语词视为存在的一部分,通过建构言语摸索存在。在言说的过程中,作者的自我一点一点地建构起来。但这个自我和通常意义上的自我很不一样:它不需要主体性,不需要回忆和念想,不需要心理和过往,甚至抛弃了自我虚构中的虚构成分。它只是一股话语流,随着话语的生成而生成,随着话语的消失而消失。话语在不断向前,自我便不断流动。自我不再需要被言说,自我即言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即言说的自我,“我”即作者。被消解的作者和我最后统合在语言中,这也应和了法国当代自我书写的趋势,即自我建构和书写过程的同一:“这首先是自我寻找的书写,正好像主体并不在书写的上游,它在当下考验自我,并在下游寻找自我”(Viart 143)。
参考文献:
[1]Authier-Revuz,Jacqueline."Hétérogénéité(s) énonciative(s)." DRIAV revue de linguistique 26(1982):91-111.
[2]Bertho,Sophie."L' attente postmoderne,à propos de la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en France." Revue d'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 4-5(1991):435-43.
[3]Bessard-Banquy,Oliver.Le roman ludique:Jean Echenoz,Jean-Philippe Toussaint,Eric Chevillard.Villeneuve d' Ascq:PU Septentrion,2003.
[4]Blanckemann,Bruno.Les fictions singulières,étude sur le roman contemporain.Paris:Prétexte éditeur,2002.
[5]Chevillard,Eric.L'Auteur et moi.Paris:Minuit,2012.
—.L' Autofictif.Talence:l' Arbre vengeur,2009.
—."Ecrire pour contre attaquer."(entretien avec Eric Chevillard,propos recueillis par Olivier Bessard-Banquy).Europe 868-69(2001):325-32.
[6]Colonna,Vincent.Autofiction & autres,mythomanies littéraires.Auch:Tristram,2004.
[7]Genette,Gerard.Figures Ⅲ.Paris:Seuil,1972.
[8]Jourde,Pierre."Les Petits Mondes à l' envers d' Eric Chevillard." La Nouvelle revue 486-487(1993):204-17.
—."L' anthume d' Eric Chevillard." Critique 622(1999):265-81.
[9]Lejeune,Philippe.Le pacte autobiographique.Paris:Seuil,1975.
[10]Lipovestsy,Gilles.L' ere du vide,essais sur l' individualisme contemporain.Paris:Gallimard,1983.
[11]Schoentjes,Pierre.Poétique de l' ironie.Paris:Seuil,2001.
[12]Viart,Dominique."Ecrire avec le soupcon-enjeux du roman contemporain." Le roman contemporain.Paris: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adpf,2002.129-74.
(《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
版权声明:CosMeDna所有作品(图文、音视频)均由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若您的权利被侵害,请联系删除!
本文链接://www.cosmedna.com/article/791116387.html